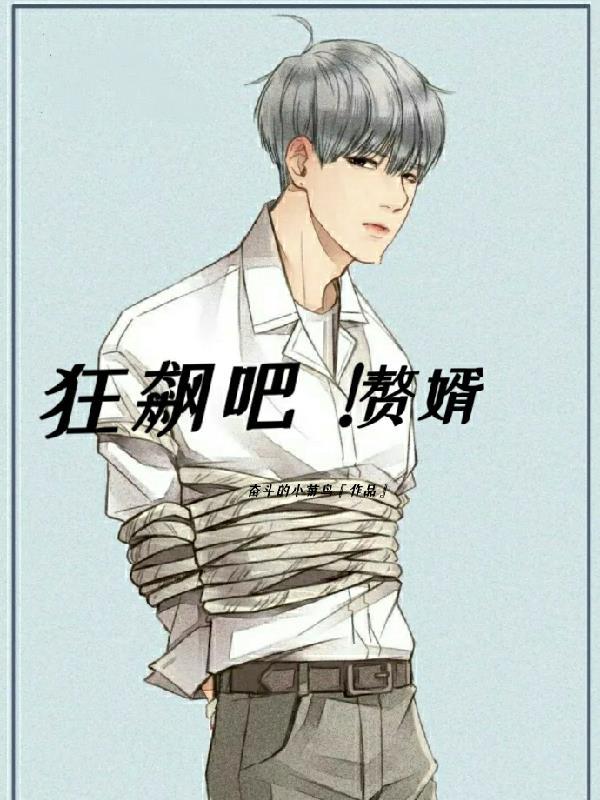UPU小说网>奈何明月照沟渠在线阅读 > 第25章(第2页)
第25章(第2页)
梁佩秋打断他的话,“你有没有想过此事败露,师父会怎么想?”
“不会的!”王云仙口吻笃定,“张大人的好友都是外乡人,他答应帮我安排好,悄悄运走,不会被现。”
“那你可知张大人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王云仙一愣,不自觉往后退了一步。
梁佩秋欺近一步。
“你可知他曾想要高价收购钧窑红,被师父婉言谢绝?你可知他曾经放出风声,谁能取来钧窑红,就许以万金?”
“不可能!”
王云仙脚步猛一顿住,迎上梁佩秋的目光,“张大人从未和我提起过钧窑红。”
梁佩秋似是无奈地笑了,师父为人老辣,怎生个儿子如此天真?
“你到现在还没明白吗?张文思伙合婉娘给你设计仙人跳,诓骗你,利用你,为的就是钧窑红!”
梁佩秋步步紧逼,“你今日敢偷天字罐,明日不就敢偷钧窑红吗?”
“不、不是这样的,张大人不是你说的这种人!”
“那他是什么人!”
她高声喝止了他。
王云仙震惊地看着她,似不敢相信面前这人竟是与他相伴数年的好友。她从未这么大声跟他说过话,也从未用这样复杂的眼神审视过他。
她向来隐忍沉默,龟缩一方火炉里,何时变得如此咄咄逼人?又如此明亮?
王云仙的心瞬时揪成一团,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但听梁佩秋一字一字道:“此人初到景德镇就大摆排场,以升迁庆贺为由头,向各大窑口索要好处。在州府任职时,曾因好大喜功不务正业被上峰不喜,多次遭到弹劾。此次明为同级调任,实则贬谪,原要下放到苦寒之地,然而经过他的一番斡旋,竟替代夏瑛大人临时调任浮梁知县。你可知夏瑛大人为何迟迟不能赴任?可知都蛮事起的缘由?可知他为何要寻钧窑红?”
她越走越近,王云仙退无可退,心几乎提到嗓子眼处,忘记了呼吸。
“你什么都不知,竟以为他是好人,真心想要帮你?你若不是安庆窑的少东家,谁会把你放在眼里?!”
这话委实是重。
王云仙当即别过头去,浑身颤抖着,仿佛有什么情绪正在升腾,但被他强行压制着。
梁佩秋也转过视线。
先前和徐稚柳提起时,见他对这位新县令似乎不喜,她便留心观察,加上三窑九会等窑务来往过几回,现此人贪财好色,不加掩饰,凡给够好处,都能撬开他的金口,不是他所说不好相处之人。
那么,徐稚柳所谓的“不好相处”,大概意思就是——不是好人。
夏瑛大人前脚刚被征调去打都蛮子,他后脚就顶替了夏大人的位子,徐稚柳思来想去,仍旧存疑,托了人前去打探。
果然,一查之下才知都蛮事起突然,而张文思近身侍从曾出现在南地,多次涉入山寨。
据夏瑛大人传来的消息,这次都蛮之乱始于一件价值连城的宝贝。
再看张文思的举动,不难猜出,钧窑红就是他许以都蛮之乱的赏金。
好个围魏救赵的法子!
其上峰曾言,张文思其人慧敏,虽贪且婪,但着实是个干才。王云仙一个毛头小子,被修炼千年的老狐狸盯上,可以说插翅难逃。
梁佩秋不气他遭人设计,不气他仗义疏财,气的是他明知安庆窑对王瑜意味着什么,却宁愿偷盗也不与王瑜交代实情。
就算他怕王瑜,难道她也不能说吗?
究竟她如何伤了他,竟让他在遇到困难时,宁愿一人承受,也不愿同她和好?
“一次安十九不够,再来一次张文思,后面还会有谁?想要设计安庆窑什么?云仙,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
她字字珠玑,句句诛心。往日听来倍觉亲切熟悉的声音,此刻却像一把刀,她每吐出一个字,那把刀就屠一次他的心脏。
他原先还苦苦支撑着,睁大了眼睛不甘于下风,待听完这席话,待看清她满眼的心疼与酸涩,他的心骤然震颤起来。
他强忍着夺眶而出的眼泪,嘴唇轻颤,吐出几个字:“佩秋,对、对不起。”
梁佩秋摇摇头,只是难过,短短时日他们之间竟有了似乎难以逾越的生疏。
她不知道究竟是谁的错?为何至此?
她弯腰将破口的天字罐捡起,那口子极薄,且极为锋利,一个不察就将她虎口划出道血口来。
可她浑然不在意似的,将天字罐翻来覆去检视,想着应该还有修缮的机会。
好在及早现,王云仙尚未泥足深陷。
这亦是万幸。
她将天字罐收拾好,也一并收拾好了心情,起身准备带王云仙去找王瑜,结果抬头一看,库房里空空如也,早没了王云仙的身影。
她立刻跑到门边,实木长条的门栓倒挂在门上,门开了一条缝,上面挂着一把铜制长口钥匙,仍在晃动中。
她心知不妙,拔下钥匙,追出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