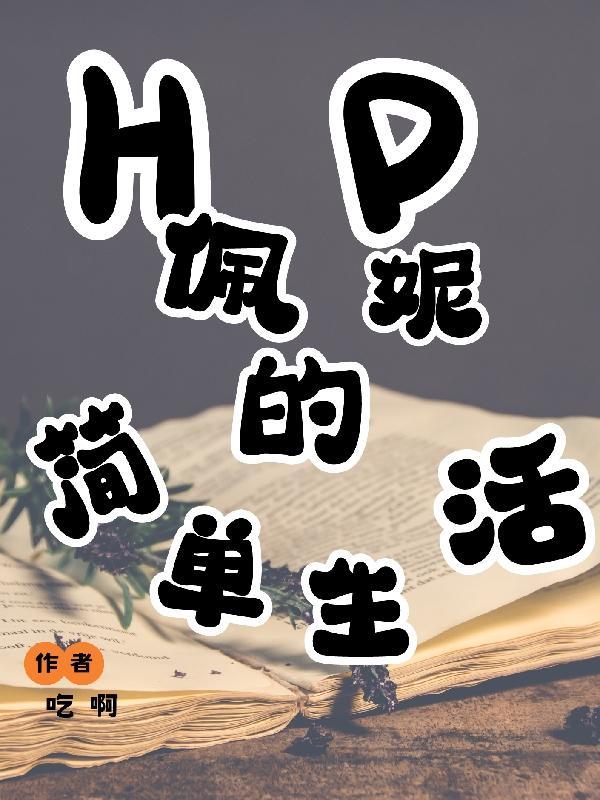UPU小说网>雪域格桑读后感500字 > 第74章 桑丁寺凶案(第2页)
第74章 桑丁寺凶案(第2页)
格桑面如土色,胡乱地把两只手往怀里揣。
传来哼哼几声冷笑,人影对一旁那个喇嘛说:“明天把这个女鬼扔到路上,让千人唾万人踹,死后下无间地狱,永世不得入善趣。”
格桑绝望地哼叫一声,倒在地上。
灯后的人厉声道:“伸出那只手。”
格桑伸出。
“不准对任何人说起此事,别人问,你就说犯了佛门大忌,受到了护法神的惩罚。”接着一摆手,那个喇嘛拎起事先备好的一把利斧,咔嚓剁下去,随即掏出一块布草草包住了伤口。
夜深了,还不见格桑回来,曲珍睡不下,焦急地坐着等。这时,门突然被撞开了,央金和一个民兵抬着一个人进来,近前一看正是格桑,面色苍白还溅有血迹,再一看左臂,曲珍着魔似惊恐地喊叫起来。
稍顷,得到通知的塔布、洛追、佳莫、小丽和旺秋等人赶来,塔布和旺秋迅给格桑洗净伤口上了药。央金禀告了经过,是在巡视中一个民兵被绊倒,才现了昏倒在地的格桑。塔布示意今晚不要惊动其他人,也不必询问格桑,央金带人暗中去查找作案现场。洛追提议由佳莫陪伴曲珍,格桑挪到他住的外屋,由旺秋和小丽看护。
第二天一早,央金在搜查寺院角落一间废弃的屋子时,现了那只断手和凶器。塔布和洛追叫上佳莫商议处理这个突事件,三人意见一致,认为对手制造凶案,是为了搅乱佛爷心智,惊吓阿婆,达到破坏坐床——起码不能如期坐床,从而造成混乱的目的。
洛追愤愤道:“这些人真可恶,竟敢将矛头对准至尊的佛爷。”
“不,央热活佛,我觉得这个人的矛头是在对准第巴大人。”
佳莫此言一出,塔布和洛追先是一惊,片刻,二人也点头赞同。
塔布攥着拳头说:“央金已找到现场,我看此案不难破。”
“大人,我看此案不必去破。对手在通过制造问题分散我们注意力,我们只要全力保证佛爷如期顺利坐床,就是最大胜利,当务之急是尽快与第巴大人会合。”
正说着,央金进来报告,在一间僧舍内现一名喇嘛中毒身亡。
塔布和洛追对视一眼,向佳莫投去赞许的目光。
“央金姐,请加派民兵保护阿婆的安全,我和小丽轮流每夜在暗中守护佛爷,请二位大人放心。”
几个人议定推迟一天启程。
当洛桑得知格桑的惨痛遭遇后,其心情之震惊可想而知,奔过去看望时,格桑还在昏迷中,他看着仍在浸血的伤口,眼里迸着火星。这时,塔布、洛追和佳莫进来,塔布禀告说:“佛爷,出了这个意外,我和央热活佛商量了,咱们推迟一天启程。”
洛桑有点惊奇地问:“大人,明天走?这件事呢?师姐的手被砍掉就算完事啦?”
洛追在一旁说:“佛爷啦,此事须从长计议。”
“从长计议?事情不查清,不抓住恶人,我就呆在这里哪儿也不去。”
事后,洛桑也为自己顶撞师父深深懊悔,表示了歉意,可当时他无法控制自己。
佳莫使个眼色,三人一同退出。
洛追提议佳莫再去劝劝佛爷。
可佳莫说:“现在只有阿婆能说服佛爷,该把真相告诉老人了。”
目前来看也只能如此,塔布和洛追都点点头。
佳莫和旺秋来到曲珍的住处。说到格桑,曲珍讲:“我早晨过去问过,她说不清,看来也不愿讲,只是含糊地说,怨自己不该摸了佛头,惹怒神灵,自作自受……”
“阿婆啦,格桑的行为是不知情开的玩笑,有人以此为借口欲达不可告人的目的。”
听得曲珍云里雾里。
“阿婆啦,六世佛爷已找到,现就住在这座寺院。”
“昨天一早就听说了,这是多大的福缘呀,可人家能见咱这山野老阿尼吗?”
“阿婆您已见过啦。”旺秋说。
“见过?没有啊,在哪儿?”
旺秋拉过老人的手说:“第巴大人已贴出通告,灵童15岁,错那宗,名叫洛桑,这回知道了吧?”
曲珍眨眨眼皮疑惑地说:“你说的是我们家赶生?孩子,可不敢开这种玩笑啊。”
佳莫拉过老人另一只手,一本正经地说:“阿婆,旺秋说的是真的,这天大的事谁也不敢开玩笑,佛爷此行就是前往圣城去坐床的。”
曲珍猛然抓紧二人的手,目光惊慌地说:“真的!?”又摇摇头,“不、不、不可能……”
佳莫赶紧上前给老人捶背,旺秋揉了揉人中和虎口穴位,曲珍呼吸均匀些了,只是目光呆滞。佳莫让老人靠在自己身上,捋着老人的胳膊和手背慢慢说:“那个塔布大人就是旺秋妹妹的哥哥,原打算到拉萨后再向阿婆说明真相的,没料到生了格桑这事,来得太突然,一时理不清也难免。阿婆啦,我们先恭喜啦,藏土众生也会感谢您的,抚育了这么有出息有才华的新一代达赖喇嘛。”
佳莫一番诚恳的话语打动了老人,停了片刻,曲珍不解地问:“第巴是尊贵的大人,他如何晓得在偏远山野有洛桑这么个孩子,又是怎么选中他的呢?”
这时,洛追和塔布也进屋了。当洛追加措从十五年前一五一十讲到眼下时,曲珍仿佛是在听一部古老的传说故事。洛追说完,半晌,曲珍才说:“央热啦,孩子能有今日,多谢您十多年来的关照,其实不用说他心里也知道。”
“阿婆啦,不用谢我,应该感谢第巴大人,所有这些都是他一手主持的,我不过是遵命行事。”
“这么说来,第巴大人与孩子有甚深缘分。”
塔布接上说:“第巴大人八岁入宫,与五世佛爷情同父子,又是佛爷开创事业的继承者,这一殊胜因缘必将传续下来。”
这么一说,曲珍忽然觉得,原来自己与这位第巴大人的关系很亲很近,她真希望能尽快见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