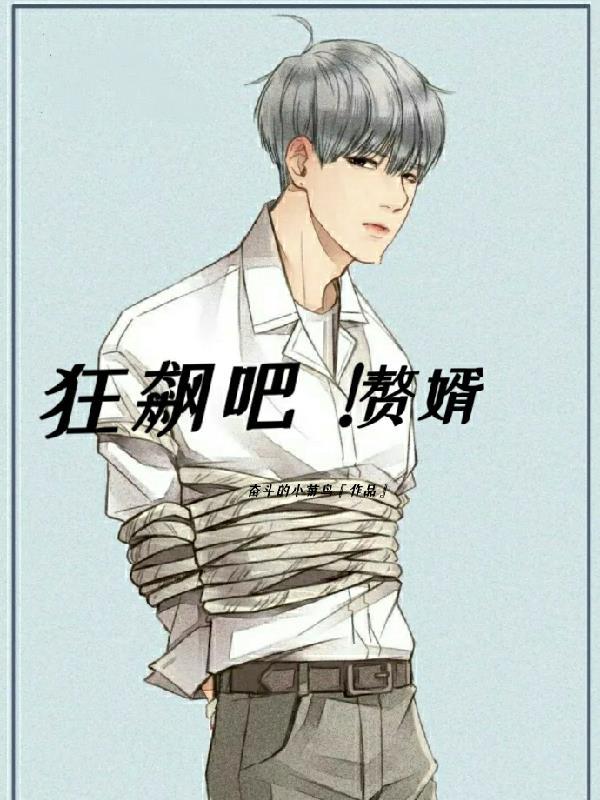UPU小说网>奈何明月照沟渠下两句搞笑 > 第7章(第3页)
第7章(第3页)
徐稚柳手腕痛,稍一动弹,就被徐忠重新压住。看得出徐忠已然半醉,手间没个轻重,那力道压下来,全然是积攒日久的怒气。
徐稚柳知道徐忠对他不满,有着许许多多的不满,不管是阿鹞的婚事,还是他自作主张书写龙缸的款识,亦或不听劝,非要和安十九对着干。
这些他自以为是的主张,想必都拂了他的面子,他作为一家之主,作为长辈,作为湖田窑真正的大管事的面子。
至此,徐稚柳明白了什么。
他安静地看着徐忠,徐忠目光微有闪烁,却强撑着没有避开,那里头布满鲜红血丝,载着老头难以启齿的尊严,徐稚柳哪里忍心?于是抬手,鸡纹小杯里的酒水被一口饮尽。
尔后他温热的手掌,轻轻包住鸡纹小杯。
徐忠则往椅子上一瘫,陡然没了力气。
安十九看了一出好戏,笑得开怀:“到底是咱大东家说话有份量,年轻人就是缺少磨炼。”
徐稚柳不置可否,转向徐忠说道:“徐叔,晚间还有祭祀活动,我先去准备了。”
徐忠点点头,没有看他。
徐稚柳环顾一圈,用眼神给诸位管事打招呼,管事们方才如梦初醒,重新招呼客人,堂口恢复了先前的热闹。
徐稚柳才要往外走,忽的小腹一阵剧烈抽搐,随即豆大的汗珠从额上滑落。
这些年来他忙于窑务,饮食向来不大规律,小腹偶有阵痛,每每用完饭食就能缓解,索性没放在心上,只这一次显然和从前不一样,来势凶猛,叫他一下子止住脚步,单手撑桌,方才能维持平衡。
这么一来,手腕用力,方才被徐忠捏住的部位又是一阵钻心的痛。
他不想被人现,勉力忍受着身体多处的痛楚,余光瞥过袖中的鸡纹小杯,嘴角不自觉微挑。
真好看呀,没有被糟蹋。
这时有脚步声靠近。
“暖窑神活动还早着,少东家且等等。”
安十九一步三晃的,走得慢悠悠,至方才几个打杂工身旁,目光扫过一桌,继而漫不经心地停在黑子身上。
打杂工们不知他是什么时候来的,也不知他听去了多少,眼瞅着方才那一出,个个缩起脖子。
唯独黑子恼他逼徐稚柳喝酒,狠狠瞪了安十九一眼。
安十九啧啧嘴:“这小子气性不小啊。”
徐稚柳移步挡在黑子身前,问道:“公公还有事?”
“无事就不能同少东家叙叙旧吗?”
“恐怕你我不是能叙旧的关系。”
“呵,少东家当真年少有为。”
瞧瞧这副清高样儿,当他是什么贱泥巴?安十九笑意越和煦:“听说你近日要回乡祭祖,左右本官没什么事,想同你结个伴,不知你意下如何?我曾在御窑厂的记载里看到瑶里盛产釉果和丕子,其开采过程煞是有趣,当地也有不少美食,遂心向往之。你若应下,龙缸款识的事儿,咱们就一笔勾销,如何?”
徐稚柳微微一笑:“公公这是威胁我?”
“哪里哪里,我只是钦佩徐少东家才智过人,想亲眼看看养育你的一方水土,领略其中风采,也好努力上进,与少东家共谋前程。”
“公公说笑了,草民承受不起。”
“当日在鹤馆,我所承诺的都还作数,少东家不妨再考虑一下?”
徐稚柳没有应答。
安十九是只骄傲的铁公鸡,显少有什么低姿态。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他主动讲和,必藏算计,他细细过一遍镇中近况,杨公有了归处,朝廷也喂他们吃了定心丸,待到夏瑛大人就任,其才干了得,安十九必不是对手。
届时功成身退,近在眼前。
徐稚柳略一拱手,作歉状:“恐怕要让公公失望了,我习惯了独来独往。且瑶里地小,无甚新鲜。”
“是吗?”
安十九似乎早有预料,并无甚失望,只眼神间流露几分遗憾,“看来我无缘领略瑶里的风光了。”
年轻学子的骨头到底是硬,比瓷石还要坚硬,既这么着,不肯弯腰,只能折断了。
安十九错身之际,附在徐稚柳耳旁,低声道:“要我说年关事多,徐忠年迈昏庸,湖田窑怕是离不了少东家。既乡下没什么新鲜,那你扫完墓可要早点回来了。”
说罢,他甩甩衣袖,大步离去。
插在堂口两侧的飞虎旗在风中猎猎作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