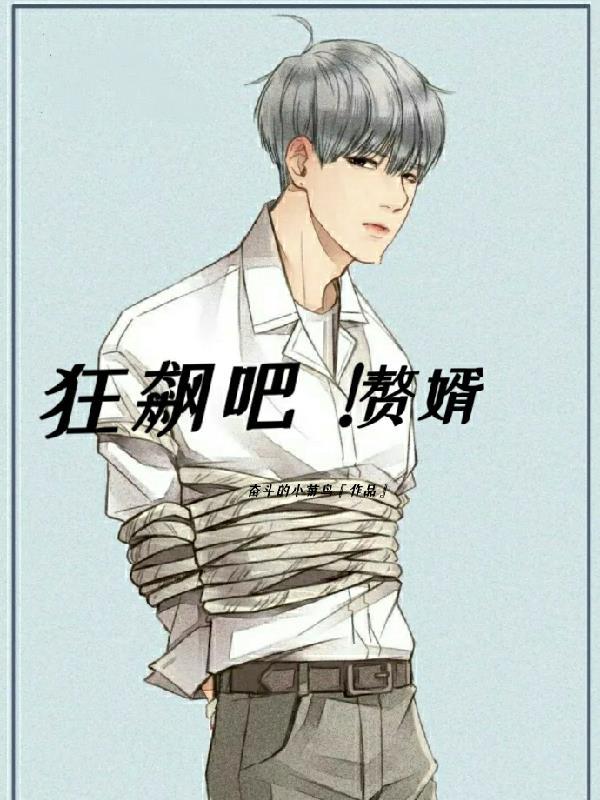UPU小说网>玄武门事件真相揭秘 > 第三章 猜测(第1页)
第三章 猜测(第1页)
"姐姐,怎么会这样?"田武泪如走珠,毕竟是才只十六岁的小孩,这还是他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面对死亡。
我坐在大弟逐渐僵硬的身体旁,"我也想知道答案。"
许弘仁此时已经离开,只剩我和小弟两人,一盏孤灯如豆,照在大弟惨白面容上,森森泛寒。
我出了会神,对小弟说道:"你把今天大弟去尚药局包扎伤口之后的行程报告来我听。"
田武说道:"哥哥今早受伤,去包扎伤口,约是在上午九时左右,回到第七路营区,因为今天不当值,他交代了我几句,就回僚所休息,傍晚时候我回到僚所,现他倒在地上,昏迷不醒,我连忙差人去尚药局请主药来诊治,结果主药验诊之后说,哥哥中了剧毒,因为拖延就医,毒素攻入心房,回天乏术。"
"主药有没有诊断出大弟中的是哪一种剧毒?"
"没有。"
我皱眉,"主药既然能够诊断出大弟中的是剧毒,又为什么说不出剧毒的名字?"
"他说哥哥有中剧毒的症状,但判断不出是什么种类的剧毒。"
我沉吟了阵,又问道:"大弟临去时候,有没有特别吐露什么字句?"
"没有,一个字也没说。"
"他在僚所休息期间,有没有人来找过他,或者他有没有去找过谁?"
"没有,今天当值的亲兵说,哥哥回僚所那阵,特别嘱咐他,说自己伤口疼痛,身子很乏,想要休息,不要让任何人打扰他,午饭也不用给他送。"
"也就是说,大弟从上午回僚所,到傍晚你现他昏迷不醒之前这段时间,他都是独自一人在,没有出门,没有进食,没有见任何人,对不对?"
"对。"
我皱眉。
田武问道:"姐姐,你在想什么?"
"我在猜测,谁是投毒谋害大弟的凶手,"我沉吟了阵,"小弟,我再问你,你们兄弟俩平时在骁果营有没有同人生过冲突,或者与什么人有过节?"
"没有。"
"这样看来,投毒谋害大弟的人,应该不大可能是骁果营里边的人?"
"我觉不大可能是。"
"那会是谁?"
我沉吟了阵,拔下头上的银钗,卷起大弟右臂的袍服,露出包扎妥当的伤口,"小弟,帮我找一把剪刀或者匕来。"
小弟抽出腰间匕递给我,"姐姐你要做什么?"
"验证下我的猜测。"
"什么猜测?"
我深吸口气,"小弟,通常来说,要投毒谋害一个人,可以有千百种方法,但这千百种方法归根结底,不外是通过两种方式,第一种,把毒液融入食品或者饮水或者烟雾中,使人服用或者吸入,经由人体内循环,毁损脏腑器官,造成死亡;第二种,直接在人的伤口上投毒,让毒液顺着血液流动,攻入心房,麻痹脏腑,使人心力衰竭而死。"
田武瞪大了眼,"这房间中没有水,没有怪味,哥哥中毒之前,也没有进食,那就只剩一种可能了:有人在哥哥的伤口上做了文章。"
"我也这么想,不过这需要验证。"
"怎么验证?"
我托起大弟的右臂,小心割开层层包裹的纱布边角,一点一点解开,现纱布的最里层还残留着些黄色的药粉,我将这层纱布小心揭下来,钗头朝前,沾了些黄色药粉,两秒钟之后,钗头变成了墨绿色。
田武脸上变色,"药粉有毒!"
我问道:"大弟有没有和你说过,今天早间是哪一位医博士给他包扎的伤口?"
田武握紧双拳,双目几欲喷出血来,"没有,但是我迟早会查出来,尚药局翻来翻去只有那么几个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