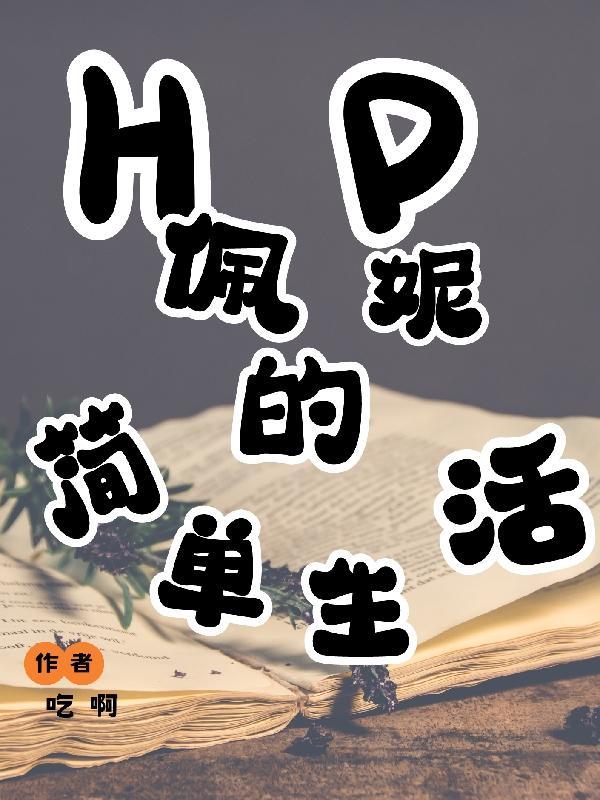UPU小说网>鸡鸣狗吠 > 第二十八章(第2页)
第二十八章(第2页)
史官再也受不住,扑通一声给他们父子跪下了。
他额头满是汗,声音飘忽,字字皆颤,“传国玉玺——确实碎于宫廷内乱。”
这件事情这样解决了。
只是阮白野还看着地上的碎玉,垂眼叹息,“可惜了,若是真的传国玉玺,五百年的流乱都过来了,今日却碎在了这里。”
阮绍奇倒不怎么在意——愤王既烧了咸阳宫,那他这一代里碎一块玉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说白了天命承袭,从来都不在玉石器物。
他比较在意其他地方,“刚玄沧那小子是不是学我笑了?”
裴齐宫里人的命算是保住了。
小皇帝满心的困惑,追在阮玄沧身后问,“祁寒——魏——阮玄沧!”
他盯着这个自己昨天之前都最相信的人的背影,声音里浸透了苦涩,“您既然已经决定舍弃我,今日又为什么还要救我呢?”
——今天的结果其实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他其实不应该再追问的,可他又实在是忍不住。
阮玄沧本来给阮鸾筝拉着胳膊走在前面,闻言示意她先停一下。
身后的小皇帝脸色在太阳底下煞白煞白,眼中的痛苦不言而喻——他的江山不是一朝倾覆的,千里之堤需要穴蚁旷日持久的蛀食,但人却总带着些侥幸,觉得坏事也许不会生在今天——阮玄沧的做作所为,就像是在堤坝上踹了最后的一脚。
“你觉得是我背叛了你吗?”
阮玄沧哂笑,“我曾对你的父亲说过:我所做的一切,从来都不是为了裴齐,而是为了我的朔川。这样的重要的事情他没有知会你,却只是告诉你早日除掉我吗?”
“我没有这样的打算!”
小皇帝着急地为自己辩解。
阮玄沧挑眉,“那他没有告诉过你:若召我进京平乱,等事情平定下来,我也不能活着,这样你的江山才可以稳固?”
小皇帝张了张嘴,说不出什么话来,只是在沉默之后小声不断重复,“我不会这样做的——”
——像是在说服阮玄沧,也像是在说服他自己。
阮玄沧摇了摇头,不再看他,回身拉住了等着他的阮鸾筝的手。
“不管怎么样,陛下,你我君臣一场,到此缘分便算是尽了。”
***
薛麟拽着阮旸来看阮青崖的热闹。
阮旸手里端着他塞过来的点心,坐在席上,看阮青崖给一圈人围着指指点点,单方面受着唇枪舌剑。
当初他们兄弟争位,阮白野棋差一招满盘皆输,让阮青崖提着刀杀光了他这一脉的男丁,人头串成一风铃,挂在屋檐上“咚噜咚噜”地闷响——独独留下了阮天宥。
人们不得其解,流言传出千百种,其中不下一半都在说——阮天宥是阮青崖的儿子——只有老子对儿子才能这么尽心尽力。
但之前阮天宥这一代直系里健全的就剩他一个,与阮青崖不对付的世家贵族心中有再多揣测,说出来也没什么用。直到现在阮白野又多了个儿子,士族就像是找到了什么倚仗一样,对着阮青崖呲出了牙——他们围着阮青崖指责,说他心狠手辣,不守礼法,有悖伦常。
而阮青崖现在不知道在想什么,手指下意识摩挲着手腕上的伤口。只是很偶尔的抬起视线,一眼锋利,戳在面前那看上去十岁左右的孩子身上——疼得那孩子差一点落下泪来。
“娘——”那孩子红着眼圈去扯褚娘子的衣袖,“我们回去好不好,我不想在这里……”
齐王、华阳公主,还有刚刚走过去的安邑郡王,这些人都长得真好看啊……可他们又比狰狞的鬼怪还要吓人。
褚娘子咬着牙,“啪“地打了他一个巴掌,”莫要与我丢人!”
小孩子捂着脸,含着泪,不敢再哭。
薛麟觉得这孩子有点可怜——他如此心软,让真的心肠冷硬一心看热闹的阮旸有一瞬间的惭愧。
阮旸问他,“陛下醒了吗?”
薛麟摇摇头,又开始为阮天宥难过起来。
“这些年他一直过得不太好,杜姐姐走了之后,就更显得没精神了。”
他看了被围起来的阮青崖一眼,“我很担心他会出事。”
——不是已经出事了吗?
阮旸叹了口气,站起身来。
“看起来这边一时半会儿也没能有个结果,我们先去看看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