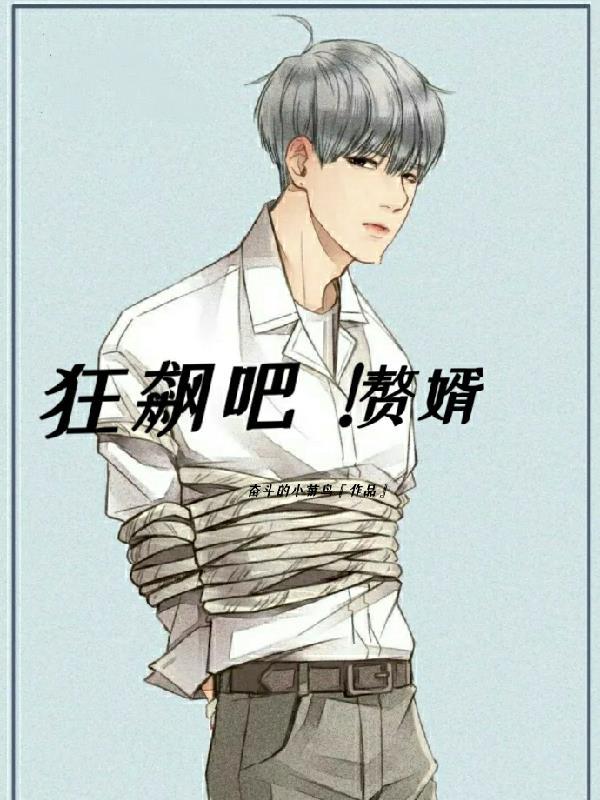UPU小说网>我本明月照沟渠 > 第81章(第2页)
第81章(第2页)
“巳时刚过。”
梁佩秋一听,起身往外走。
她动作熟稔地抄起拐杖,甚至不需白梨搀扶,走得又快又稳。白梨落后一步,小心伺候在她身旁。
她急了,推白梨向前:“你跟着我做什么?快去把人赶走!”
“哦哦。”
白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动作比脑子快,下意识转头就跑。
从去年断腿到如今,她跟随梁佩秋有一年多了,尚算了解她的为人,是再亲和不过的,向来没什么脾气,碰上胆大的奴才,甚至可以把她当软柿子拿捏。
只自从王大东家在祠堂自杀,一切就变了,窑口气氛怪异,人人阳奉阴违,偌大的家业她需得不眠不休才能操持得当,自此不再爱笑,也不多话,脾气易怒,阴晴不定。
对内是“东家”,对外是“大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容不得一点反驳,稍有不慎就要挨板子。
她倒是没被揍过,只凡事犯到那位太监跟前的,都受到了不小的惩罚。这么一想,她忽而想起什么,大步朝外跑去。
梁佩秋到门口时,安十九刚好从软轿中下来,裹着一张上等狐狸皮,细白的脸像女子一般秀美。
她上前恭迎,安十九轻笑:“早就和你说了,你腿脚不便,不必亲自相迎,怎不听呢?”
“不要紧,坐了一晌午,出来迎迎大人,也正好松松筋骨。”
安十九就喜欢听她说话,坦诚直接,不比前头那位大才子圆滑,整天打官腔,交往起来累死个人。
他推开左右,上前与梁佩秋并肩而行,说道:“雪天路滑,还是得当心。我让人给你送的草药,可还一直用着?”
“每日都在用,疗效很好,还未谢过大人。”
“你我之间客气什么。”
安十九正笑着,余光瞥见一道疾冲上前来的身影,还没来得及躲闪,那身影就被高壮护卫一胳膊撂在雪地里。
他惊魂未定,拨开油亮的狐狸毛定睛一看:“哟,这不是徐大才子跟前的书童吗?好些日子没见,你躲到哪里去了?”
“我呸,你草菅人命残害忠良都没躲,我为何要躲?”
“你就不怕你主子原先的仇家要了你的命?”
“我家公子品性高洁,哪来什么仇家?再说了,要也是先要你的命!若非公子仁义,一直没对你下狠手,你早就被打派头弄死一千次了!哪由得你猖狂至今?”
前朝时童宾以身蹈火,舍身取义,引众怒,老百姓高举义旗动民变,将太监潘相拉下马背处以极刑。从那之后,景德镇出现过好几次大型罢工游行,每次罢工的胜利,几乎都要牺牲领头,久而久之,民间就将罢工称作“打派头”。
时年朝他啐一口痰:“狗太监,潘相就是你的下场!你别得意,迟早要遭报应!”
“是吗?”
骂他狗太监,还诅咒他遭报应,这要放在平时,安十九早就不跟他废话,直接叫人拖下去乱棍打死了,可今日好似很有闲情逸致,转头问梁佩秋,“我记得以前你们常在鸣泉茶楼喝茶,关系不错?”
梁佩秋扫了眼被两个大汉反剪胳膊按在雪地里的时年,轻描淡写几个字:“逢场作戏罢了。”
时年一听,整个人奋力反抗起来:“梁佩秋你个畜生,你说的什么话?公子对你有多好,你全都忘了吗?你的良心喂狗了吗?你怎么变成这样?”
年前他回瑶里给阿南送公子的旧物,多是一些书籍手札,临行前她还给他摆了践行酒,让他今后远离是非,不要再回来。
她答应他会好好活着,他才放下心来,决定以后跟着阿南,给阿南当书童,可到了那里,阿南却说这里更需要他。
他想到那个瘫在黑夜一蹶不振的少年,想到在枯萎的荷塘和冷清的狮子弄日日夜夜徘徊的孤影,想到公子多年以来如履薄冰、每一颗落子无悔才逐渐壮大起来的湖田窑,想到死去的黑子和活着的旧友,咬咬牙,还是回来了。
可等待他的是什么?
“梁佩秋,你做这样多的亏心事,不怕夜里恶鬼找上门吗?不怕将来到了地下,无颜去见公子吗?你……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时年紧咬牙关,憋足一口气挣开左右束缚,大步冲上台阶,“你说啊!今日你要不给我一个交代,我就一头撞死在你门前!”
话没说完,他就被护院重新拽了回去。
时年太瘦了,像个麻袋被拖来拽去,摁在雪地里两片肩胛骨高高凸起,脸也变了形,只一双眸子亮得吓人。
梁佩秋看着他,犹如在看一个陌生人,目光冷淡,神情麻木。
“有什么为什么?识时务者为俊杰,谁不想往上爬?”
“我不信!我不信!”
她不是那样的人啊,公子怎会看走眼?时年大叫:“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是不是那个死太监逼你的?他逼你害死了王瑜,是不是?”
他想到阿南,认定安十九故技重施,用家人性命相威胁,刚要破口大骂,就被梁佩秋堵了回去:“不是你想的那样,安大人没有逼我,从始至终我只是在利用徐稚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