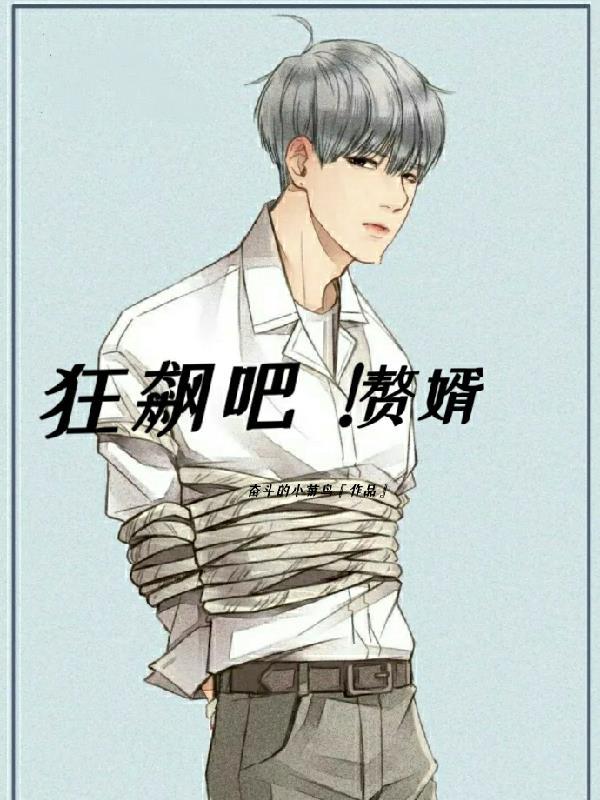UPU小说网>名犬番外 > 第44章(第1页)
第44章(第1页)
想到这人的胳膊被打了个大窟窿还不老实,边亭恶声恶气地威胁,“再闹出什么幺蛾子,我不会再救你了。”
“好可怕哟。”靳以宁的记忆已经回笼,想起了昏迷之前发生了什么事,他配合地抖了抖,安心地靠回边亭的背上,有些虚弱地骂了一句,“小心眼。”
边亭没有回嘴,闷头往前走,不再开口说话,一方面是为了保存体力,另一方面他不想和靳以宁废话。
只是走着走着,边亭察觉到靳以宁的体温越来越高,像一只火炉似的,烤得他的后背发烫。
“靳以宁?”如今边亭已经很习惯直呼老板大名,“靳以宁,听得见吗?”
“嗯?”靳以宁的脑袋动了动,灼热的呼吸烫得边亭的耳朵也跟着一起烧了起来。
“你体温很高。”边亭这下更加确定了,靳以宁确实发烧了,“感觉怎么样?”
“嗯。”靳以宁应了一声,很快又将脸埋进了边亭的肩上,“不碍事。”
在这种情况下发烧,可不是闹着玩的,边亭加快脚步,试图找到一个可以短暂栖身的地方。但再往前走就要进入茂密的森林,暗夜行路不是什么好主意,如果在树林里迷路了,情况会更加棘手。
就在边亭一筹莫展之际,幸运之神再次降临。边亭刚拨开一丛拦路的芦苇,一个小小的棚屋毫无预兆地,出现在了他的视野中。
屋里没有亮灯,看不出有没有人,安全起见,边亭把靳以宁留在屋外,自己先进去检查了一圈。
这间小棚屋很旧,应该是附近的钓鱼爱好者临时搭盖的。屋子虽小,但五脏俱全,里面除了一些钓鱼的装备,还有不少生活物资。
边亭打开架子上的太阳能灯,又用屋主留下的柴火烧起了暖炉,然后把靳以宁带进了屋,在墙边找了个靠近火炉的角落,将他放了下来。
安排靳以宁躺下之后,边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剥他的衣服。
靳以宁浑身的衣服都已经湿透,这会儿又发着烧,这身湿衣服不能再穿了,恰好屋主在这里留了套换洗的旧裳,于是边亭就想着先帮靳以宁换上再说。
只是没想到靳以宁这人平时成熟稳重人五人六的,生起病来竟比小孩还任性,边亭好心帮他脱掉下外套之后,他说什么也不肯配合了。
“你干什么?”靳以宁攥着边亭的手,一脸警惕。
“先把湿衣服脱下来。”边亭保持着最后的一点耐心,“这里有干的可以换。”
靳以宁瞟了眼架子上搭的t恤运动裤,开始无理取闹地挑剔道,“不好看,不穿。”
话撂下了,他脑袋一歪,就开始装死。
“好,随便你。”边亭懒得和他废话,由着他穿着湿透的衬衣西裤。自己则换上了那套不好看的“衣服”,把火炉的另一头坐下了。
屋外的风又开始大了起来,刮着屋顶上的塑料棚布簌簌作响。炉子上烧着快要开了,噗噗往上冒着热气,白茫茫的蒸汽和跳跃的火苗一起,温暖着这方寸之地。
在兵荒马乱的一夜后,这间陌生的小屋,和这从微妙的火光,竟能给人一种奇异的安全感。
边亭曲着双腿,将下巴枕在膝盖上,目光专注地盯着火苗发呆。
他知道自己应该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但在精神和肉体双双松弛下来之后,他反而睡不着了。
就这么枯坐了好一会儿,边亭伸长腿,拨了拨靳以宁的手背,没大没小地“喂”了一声。
靳以宁没有反应,但他知道他也没睡着,因为呼吸的节奏是骗不了人。
边亭问他:“你刚才在江里的时候,是不是不想活了。”
靳以宁睁开眼睛,他果然还醒着,火光遮掩了他脸上的病气,仔细望去,眼底还有光芒在隐隐浮动。
“我为什么不想活了?”靳以宁觉得边亭的这个问题很没有道理,“我位高权重,家财万贯,钱多得十辈子都花不完,为什么不想活了?”
听他这么说,边亭嘲讽地笑出声,收回了腿,大逆不道:“你最好是。”
“脾气真差。”靳以宁佯装无奈地叹了口气,眼尾“楚楚可怜”地垂了下来,模样看着像是被伤了心:“长大了,翅膀硬了,现在连乖也不愿意装了。”
边亭懒得和他装模作样,鼻子里冒出一声冷哼,将坏脾气践行到底。
几句玩笑话后,气氛放松了下来,靳以宁却在这个时候,毫无预兆地提起了在船上时没有聊完的话题,“那么今晚,你为什么会摸进江旭耀的房间?”
“今天早些时候,我在甲板上听见江旭耀打电话,他在电话里提到很多次你的名字。”好在边亭不是毫无准备,搬出了早就编好的答案,“我怀疑他想对你不利,就找机会进他房间,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
“没想到你对我倒是用心。”靳以宁唇边的笑意似有似无,看不出他是否相信边亭的这个解释。
边亭无视他眼中明晃晃的嘲讽,反问靳以宁:“你又是为什么会在他的房间里?”
“我早就知道他有问题,这次来他的婚礼,就是想探探他的底。”靳以宁拿出的说辞,几乎和边亭一致,“于是就用了点关系,复制了他的房卡和指纹。”
边亭听完,没有究根问底,因为他给出的理由看似合理,其实也经不起深究,他不想再把话题引回自己身上。
炉子上的水正好在这时烧开了,蒸汽“咕噜咕噜”顶着壶盖,边亭顺势中止了谈话,伸手拎起壶子,将水倒进一个看不出干不干净的杯子里,待稍微凉了一点之后,递给了靳以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