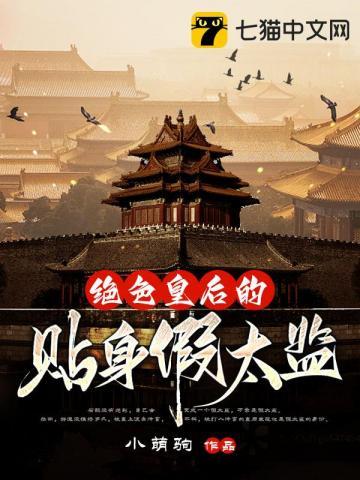UPU小说网>日月长明番茄加糖笔趣阁全文免费阅读 > 第81章(第2页)
第81章(第2页)
外面漫天大雪纷纷扬扬,远近高低都被覆上了一层银装。
高炎定呼出一口白气,暂且将身后那些乌糟的事摆脱了个干净,他走到停在树下的马车旁,见车窗边紧挨着一大一小两个脑袋,视线却不是落在自己身上,而是望向不远处一辆低调的车驾。
他认出正在登车的人正是先前被秋家纨绔招到狱中陪酒的小倌。
明景宸眉梢处凝着冷意,眼底夹杂着根深蒂固的厌恶,他看了一会儿,见高炎定走来,便低头和涣涣说了些什么,一大一小默契地钻回车里,将帘子放了下来挡住了高炎定的目光。
高炎定转身又去看那辆绿呢马车,车夫扬鞭挥了几下,马儿嘶鸣一声跑了起来,车驾渐行渐远,很快消失在风雪之中,只在雪地里留下两道深深的车辙印。
他站在风雪里出了许久的神,心想,莫不是秋家狎亵小倌的事让景沉想起了曾经给天授帝当娈宠的事吧?
想到明景宸可能的遭遇,高炎定又疼又怜,只想千百倍地对他好,从而弥补那些糟心的不公。
涣涣被明景宸指派到车窗边,悄悄掀开帘子一角只露出一双黑葡萄似的眼睛朝外张望,然后眼睛蓦地睁大,一下缩回车里躲到明景宸怀中,道:“叔叔冻成雪人啦!”
明景宸心头一跳,立马亲自去看,只见高炎定头上、身上落满了雪,像是披了一件白色铠甲,一动不动地立在飞雪中,仿佛魂灵出窍了一般。
“高炎定——”明景宸喊了一声,又怕他真出了事听不见,便让涣涣老实坐在车里不许动,自己跳下车朝他跑去。
雪天路滑,他又跑得着急忙慌,脚下一滑,扑在了对方身上。
高炎定一把搂住他,“跑出来做什么?”今年的雪下得尤其大,芦花似的闻风而舞,不过一会儿功夫,明景宸的眉毛、头就被染成了冰雪的颜色。
高炎定替他拂去,可那雪纷扬不止,很快又变作白色。
他忽而想起一句话,霜雪满头情同白。
想到此,他心中波澜横生,恨不能就这样与对方天长地久下去,却又担心这般大的风雪真把人给冻坏了,连忙压下那点子旖旎情思先把人带回了车上。
擦干净身上的雪,明景宸还在想方才高炎定在风雪中的异样,他抬眸去看对方,不想对方也正在打量他。
那目光像是能融化铜铁一般异常炽烈,不过是视线碰撞,就烫得明景宸险先惊跳了起来。
高炎定以为他冷得抖,连忙将丢在旁边的大氅重新给他披在身上,又塞了个手炉在他怀里才稍稍放心些。
马车跑了起来,碾在积雪上出厚实沉闷的响动,外头北风呼啸,如同野兽嘶嚎。
涣涣坐在明景宸怀里,两大两小四只手一起捧着手炉取暖。
她晃悠着小脚闹着要听故事。
明景宸拿她没办法,敛目思考了会儿,开始讲了起来。
高炎定偷听了几句,现对方正在用一种诙谐易懂,很能勾起小孩子好奇心的话语在给自家侄女儿讲临江之麋的故事。
讲到结局麋鹿把自己当成了狗,跑出去却被外头的野狗咬死了的时候,涣涣害怕地用手遮住眼睛,扭股儿糖似的钻在明景宸怀里不敢抬头。
明景宸笑着拍了拍她的小屁股,轻哄了几句才算好了起来。
没想到怕归怕,这样新奇的故事涣涣之前从来没听过,非要拉着他再讲一个。
明景宸戳戳她的腮帮子,假意嗔怪道:“那再说一个老鼠的故事,听完可不许再闹腾了,听到没有?”
涣涣眨巴着圆溜溜的眼睛,点头如啄米。
高炎定又竖起耳朵偷听,然后额角青筋抽搐了不断,现这个所谓的老鼠的故事,竟是永某氏之鼠。
高炎定:“……”
给五六岁的奶娃娃说这种讽刺意味极浓的故事,对方能听懂么?别真给吓哭了。
他这边忧心忡忡,可到最后涣涣非但没害怕,反而笑得咯咯作响,花枝乱颤,依偎在明景宸怀里和他好得不得了。
他越看越眼热,心里酸溜溜的如同酿了十来车陈年老醋,自己泡在醋坛里,酸得直冒泡。
高炎定哀怨地望着那一大一小亲亲热热的样子,谁承想,正与涣涣玩闹的明景宸忽然抬头瞧了他一眼,脸上似笑非笑,眸里却一丝笑意也无,只有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