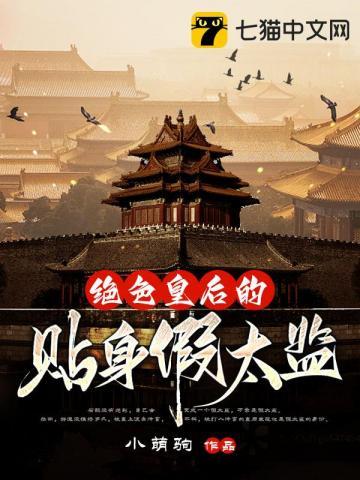UPU小说网>瑰华是什么意思 > 第十九章 姊弟谈(第2页)
第十九章 姊弟谈(第2页)
瑰里手上一滞,随后道:“上回不是问过了吗?”
定南一贯都是个善察微毫的孩子,听瑰里这样说,他也就明白了,心中却不知是喜还是忧。室内再次静了下来,瑰里已经开始写另一篇《燕燕》,定南却感气氛有些异样,搜肠刮肚着寻找话题。他问道:“你和拾兰堂姊,怎么样了?”
瑰里停笔,将笔架在笔搁上,道:“没再见过了,也没有书信。”
定南犹豫了一下,瑰里见状一笑,道:“你肯定是在想,她是嫡公主,又有卫王后权威似天那样的母亲,我就不怕与她生了隔阂断了自己的后路吗?”
定南点点头,担忧地道:“这正是我所担心的。但拾兰堂姊向来宅心仁厚不计前嫌,也善解人意,或许会好些吧。”
瑰里叹了口气,道:“我曾试着去做长姊那样的人。她向来波澜不惊,喜怒不形于色,为人又十分退让和谨慎。但我渐渐发现,我做不到。”
定南也认同道:“是啊,而且自从她嫁给姊夫,就一直在避着卫骅哥哥呢。要是我,我定是过不去心里的这道坎的。这么说,她是不爱卫骅哥哥了吗?”
瑰里摇头道:“不知道,但她定不想为长子府和自己招来制造流言的机会吧。有的时候也是奇怪,随随便便一个毫无来头的事情在大京就能传得有鼻子有眼。”
定南思索道:“没错,大京向来如此,甚至现在比方立国之时还要厉害。大琰发展得越好,就越有一些闲不住的人开始闹事了,开始利用各种手段政权夺位。”
瑰里带着些许赞赏地道:“南儿最近是真在用功啊,定是读了不少书。将来立足朝堂,要好好为大琰效力啊!”
受到阿姊如此夸奖的定南似有些受宠若惊,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他的用功劲,可是从来都不敢和瑰里相比的,至于说到效力大琰,看来阿姊很是寄希冀于他啊。
();() 姊弟二人似就这样给此事下了定论,聊了一些其他事情之后也就熄灯各自去睡了。奈何他们谁都不是璴里,她内心深处的想法谁也不知道。
对于现在的璴里来说,她是否意识到夫君萧长霖那个危险想法的存在,是否了解他那为了夺权不惜牺牲一切的野心,以及是否明白多方势力如同水火不能相容,大京中央必有一战。
这些,远不是儿女情长所可以比拟的。
若说璴里出嫁前便很懂事,那也仅是明白阁中之事,军政皆是纸上谈兵;可嫁入王室便如同踏进虎穴,使昔年一个温柔的少女也渐渐向成熟的妇人转变,被迫去学着打理和调整那上上下下的事务,还要帮着夫君观察情势。
四年中,所有人都变了。正如卫骝所说,时世上的谁都会被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所改变的。或许最后可能会因为什么与他先前最爱的人为敌,固然可凄,但最初的那份真挚,是怎也不会被消磨殆尽的,总还有一丝余情在。这份余情虽不能改变他的行事方向,却能软化他的心。
第二日,瑰里早早就起床了。她稳稳地跪坐在梳妆镜前,望着镜中自己精致的妆容,忍不住满意地微微一笑。此时女淑正在为她一遍遍梳着她如云的齐腰秀发,抬头看到她的笑容,也不禁夸赞道:“小姐今日真好看。”
发髻编好了,梳头婢女们皆停下了手中的工作。瑰里笑着对镜左右欣赏自己的头发,似怎也看不够。此时青棠捧上一盘子珠玉首饰,笑着道:“小姐挑挑头饰、珥饰和镯子吧。”
瑰里拿起几个来回比对,道:“在我印象里,阿姊当年可没有我这样爱美。”
青棠赔笑道:“哪里哪里,大小姐爱美的时候,您是没见过呢,只有信秋姐姐最懂她的梳妆风格。”
女淑替她插上一对青花步摇,也道:“是啊,若不是今日去令府做客,还要见到卫三郎君和许多卫氏族人,您可从来都不会花这般长时间梳妆的。”
“是啊,今日见郎君,妆容打扮上如何疏忽得了?”众人回头,见卫氏正由侍女白岢扶着掀帘进门,瞧着瑰里这一副欣喜的样子,便接话说道。瑰里脸一红,不再去说话,只是低头为自己戴上了一对白玉耳环,侍女们见状也都窃笑着,卫氏更是坐在了茶桌旁,打量着瑰里今日的装扮。
侍女为瑰里找出了一件赭红色镶金边的长裙为她穿上,裙子微微拖地,甚是优雅。平日穿惯了过膝短裙和靴子匹配的骑装,今日实在是不大习惯,觉得这裙子怪拖沓的。
瑰里在镜前盈盈舞动一圈,最后又笑着看向卫氏,似在等她的评价。刹那间卫氏心中有些恍惚,女儿的容貌,与她是极为相像的,瑰里今日的妆容,使她梦回二十年前她嫁给萧锵的那一天。那天她头戴金冠和闪闪的步摇,车轿仿佛陷在了红色中,前来贺喜的人全都挤在府邸前,乐音和锣鼓相交杂,她满饮一小杯礼酒,便被抬着进了元和门。那场景,终生不忘,魂牵梦绕。
她希望,她的女儿将来也能这样风风光光地嫁给如意郎君。
卫氏欣慰地笑道:“很好,佳节宫宴都没有今日正式。我的女儿将来,可不知要吸引多少人羡慕的眼光。”
瑰里在镜子前仔细打量自己身上的每一处,确认它们必须是完美的,结果也确实令她满意。这身衣服在穿上之前早就叫人去熏了香,如今正散着幽幽的清香,煞是好闻。瑰里欣喜地不知如何用言语来表述,她笑着辞别卫氏,跑出门寻定南去了。
见侍女们都出门送瑰里去了,卫氏脸上的笑容瞬间沉下来。她挥手唤来了守在门口的女淑,低声问道:“长子府最近有没有什么新消息?璴里如今怎么样?”
女淑知道,卫氏最想问的是大小姐的身体状况,回道:“信秋同我们一直有联系,她说近来大小姐心情还好,身体调理地也不错。但毕竟先前受人暗害,生产时便受了伤,恐难再孕。”
卫氏每听她说一句,怒火便旺一分。她强抑着这股烈火,问道:“璴里可知这其中的真相?”
女淑道:“大小姐定是派人去查了的,但只是齐国公主查清此事后便封锁了消息,她不太可能知晓的。况且,虽先前大京隐隐有关于此事的流言,但知道大小姐是受害的人并不多,这些人、包括那流言,都让齐国公主给锁的死死的。所以整个大京知晓幕后之人的人,恐也就您、卫王后和齐国公主了。”
卫氏点头,想着这萧葛兰行事果真刚刚好,既帮了她也帮了自己。她转而问道:“关于王长子呢?他和璴里的关系如何?”
女淑道:“听闻王长子对大小姐一直是既不亲密也不疏远的态度,但大小姐也从不向他索取宠爱。倒是齐国公主,很想与大小姐热络。”
卫氏闻言脸色一变,瞬间对此事提起了重视。在那么一刹那,她似乎有些后悔将璴里送到深宫那样阴而险的地方去了。险象环生,璴里能否熬到成为王后的光辉时刻?这之前的每一步,都如履薄冰、如步刀尖。
卫氏很了解卫王后,而她的长子恰好与她性子相同。萧长霖是一个多么好妒而善于伪装之人,他肩负大任却心狠好杀。卫氏不求他能够爱上璴里,只希望璴里和辟芷院是安全的。
卫氏挥挥手,吩咐道:“给我梳妆,趁着瑰里和定南不在,我去见一见璴里。”
女淑垂首应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