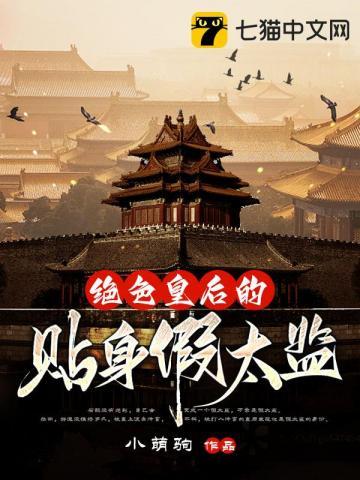UPU小说网>喜相逢有过户成功的吗 > 第55节(第1页)
第55节(第1页)
高处的守城军拿擂石、弓箭来对付他们,骑兵也在人群当中驱驰追赶。几万灾民,若有个组织部署,未必没有破城的办法,只是这样毫无方向乱冲乱撞,面对大批甲坚兵利的马步兵,自然不是对手任人围剿,一时不知多少人在马蹄下被踏死。
赵蘅和玉行也知道这是唯一能够进城的机会,在人群当中且伏且逃,玉行拉着赵蘅往一旁壕沟里跑去,不料背后冲来一个被箭射着眼睛的人,一路嚎叫一路双手在半空乱抓,把两人冲开了,赵蘅也摔倒在地,玉行回头想去拉她,却又有一块火石砸下。
赵蘅伏在地上,刚抬起头,便发现身后一匹黑马四脚抬高朝她压来,玉行冲过去将她拉到怀里,两个险险从马蹄下滚开。
那都侯被惊了马,气愤地回头就是一刀落下,被护在身下的赵蘅看到寒光闪过,紧张地高喊了一声:“傅玉行!”
都侯听到了,收刀抽身,将马勒着在原地转了个旋。此时其他灾民也多数被军队控制住,防线前倒下了大片尸体,后面的人便一点点被成排的枪尖逼退,重新退回茫茫的雪地当中去,像一缕一缕淡色的幽魂。这些幽魂要漂到哪里去,没有人关心。
那都侯再度踢着马过来,一排士兵也上前把两个人团团围住。玉行把赵蘅挡在身后,都侯看向她,“你刚才叫他什么?”
赵蘅没有说话。
都侯又看向玉行,“你是宣州城养心药堂的傅玉行?”
赵蘅抓紧玉行衣袖,让他不要承认。
玉行看着周围森冷的刀尖以及满地尸体,不知这些人有何打算,最终还是道:“是我。”
那领头又把眼睛将他死死盯了半晌,点点头,道:“我们指挥使大人最近正有意寻找一位医术高明的大夫。傅大夫,随我来吧。”说着,朝身边士兵给个眼色,自己踢着马走了。
几个士兵立刻站到面前,围出一道路来,示意傅玉行跟上,完全没有商量的意思。赵蘅有些不安,玉行用眼神让她跟在自己身后,谁知那士兵又伸刀将赵蘅拦下,冷脸道:“都侯只吩咐一人跟去,闲人不许随行!”
玉行道:“她是我妻子,无论如何不能舍下的,让她随我一起去吧。”
赵蘅看他一眼,没有反驳。
那士兵却还是不近人情:“你当指挥司衙门是什么人都可以进的吗!”
玉行也不让,索性冷声道:“她是我妻子,而且怀有身孕。你们要么让她跟着我,要么就地杀了我。”
那几个士兵相互看看,最后收起刀来,示意二人同去。
一进指挥使司衙,便一点也感觉不到冬日的严寒了,处处都是炭火地龙,催得连院中牡丹都在这种季节开得艳丽。一路雕梁画栋,富丽堂皇。赵蘅和玉行还被带去沐浴更衣过,才被允许去见那位邓州军指挥使。
指挥使康元义呈大字型躺在床上,一只脚垂到床下,敞着衣襟,捂着脸,也分不清是活着死了。
都侯到床前低声道:“大人,你提过的那个姓傅的大夫,我们带来见你了。”
康元义一动也不动:“带进来吧。要是治得好,自然有赏;治不好,照老规矩处置。”
都侯转头道:“听着了?若你治不了我们大人的病,你连你的妻儿都别想活命!”
傅玉行没理他这番话,看病救人根本已是家常便饭,如常号脉,如常诊断,如常放血、施针、开药。第一天晚上,那康元义还恹恹不振,到了第二天,就有专门的仆婢来请二人去见他了。对方精神大好,对玉行的态度也和善许多。
“果然还得是养心药堂的名医。之前几个,说我是什么湿热邪气入体,又是什么痹症,针扎了一回又一回,药吃了一碗又一碗,就是不见效。我一时气不过,处置了几个。如今看来,是天不亡我。”
傅玉行只礼貌性地勾勾嘴角,“这痈疽之症是长期饮食肥甘厚味,湿热之邪内生所致。不过因你体质强健,初起时症状不显,其他大夫误诊为痛痹之症也是有的。何况大人口口声声说治不好就要杀了看病之人,那些大夫自然心慌意乱。我想,往后最好不要在治病之前威胁大夫性命。今日我还能对你的病症起一点作用,所以才被带进这座官邸,否则,我们也不过是那些被赶出城外饿死的灾民之一罢了。”
康元义一笑,“傅大夫听起来,是对我把灾民拒之门外的事情有点意见?”
傅玉行客客气气道:“不敢。”
康元义顺势将手一挥,很大方地做出了不计较的神情:“傅大夫你一介平民,哪里懂得我们为官做将的难处,国家大计可不是你们以为的那么简单。一个百姓饿死只是一人饿死,可军人饿死就是一国将亡。我省下这些粮食,也是为了让军人有饭吃,到时燕勒人来了才能打胜仗。虽然残忍了些,却也是无奈之举,为了社稷,我是情愿担下这个骂名。”
傅玉行眼皮搭着,似笑非笑的,一句话也没回。
康元义又问自己的病多久能治好,玉行对他说完接下来医治的计划,对方大为高兴。当天晚上,两个人的待遇就从地牢转到了花园旁的大屋子里,连属下对他们也变了一副脸色。
晚间给他们的饭菜有羊肉馒头、酒蒸白鱼、薤花茄子、黄糕糜,自从逃亡后,再没有见过这样一顿饭,味蕾甚至受不住油荤了。然而一面是这官邸内的鲜衣美食,一面却是寒冬里被赶进雪地的几万流民,想到他们一天前也在那些流亡的人群之中,就觉得心绪复杂。
赵蘅拿着筷子,道:“你看,这邓州城究竟守不守得住?”
玉行根本连筷子也没动过,只是盯着桌上的烛火,最后说了一句:“咱们得走。”
第二天夜里,梆子敲过二更时,房间内的二人听到外面传来着火的呼救声。
赵蘅知道,她白天趁傅玉行看病时,偷偷绑在马房里的一根蜡烛已经烧断麻绳,掉到草堆里去了。
趁着守门的人都到了外面灭火,赵蘅和玉行溜出房间,一路摸到了后院围墙,围墙离外墙极近,顶上有一道年久失修松动的缝隙。傅玉行先翻上去,上去后又把赵蘅接上去,他再到下面接住她。过了围墙,又躲过巡逻的卫兵,照样翻过外墙。他们这一路步履艰难,唯有这晚逃出指挥司衙却是异常顺利。
就这样一路从司衙后街逃进后面的暗巷,想要找到去邓州码头的方向,只等天一亮便上船。然而二人对邓州地势不熟,在暗巷里绕了许久。
走到一处巷口时,迎面却正看到街上迎来一队长长的火光。傅玉行立刻把赵蘅拉回黑暗里,还以为是康元义派来搜寻二人的。
赵蘅躲在傅玉行背后,等那些火光靠近了,她感觉到傅玉行的身体也僵硬了。
“怎么了?”她抬头问他,却被傅玉行抬手按了回去。“不要出声!”
那一队火光,竟不是本城军队,而是燕勒军。
从城门方向一路到此,看不到尽头的燕勒军,脚步擂擂,盔甲铿锵,就这么如入无人之境,直插进城市中。——那个在他们面前号称军贵民轻报国无门的指挥使,在敌军临近之时,毫无抵抗,开门迎敌。邓州百姓就这样在毫无自觉的情况下,成为了燕勒遗民。
二人都手脚发凉,与其说是恐惧,不如说是感到一种彻底的坍塌。
玉行拉着赵蘅继续往后逃,躲开燕勒军队。天亮时,又到了城后一处贫民聚集的废墟里。周围昏暗破败,赵蘅进到屋里,不知怎的,总感觉周围悉悉有声。她一抬起头,险些没叫出来,原来房梁上密密麻麻藏了十几个人,再一看,都是寻常百姓打扮。
双方彼此看清后,那十几个人也从房梁上下来,都是内城逃出来的。听他们所说,昨晚指挥使就连夜把官邸都让给了燕勒人,如今城墙上方都已经插遍燕勒军旗了。天还没亮,燕勒人就开始挨家挨户勒索钱财,有时是拿了钱就走,但见了女子照常是要掳掠的,有时嫌婴孩吵闹,索性杀了了事,全凭一时心情,真正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赵蘅和玉行原打算穿过内城,去城西的码头坐船,其他人连忙劝道:“那怎么能行,整个内城早已经被燕勒人把守住了,怎么可能从他们眼皮底下过去?”
邓州城三面围墙,只有东面是以一条山脉密林作为分界,玉行发现那山林就在废墟不远之外,肉眼可见的距离,如一片黑云压在雪上。他才提出穿过山林出逃,其他人又纷纷摇头颤栗道:“那山里有老虎吃人,而且积雪深厚,地势复杂,一进去就会迷失方向,就是熟悉的猎户也不敢在这种天气进山哪!”
“死在贼兵刀下难道就好过死于猛兽之口吗?”赵蘅虽这样说,其他人还是不摇不动。他们用熟悉且笃定的表情向她表明,那座山之所以能成为邓州的边界,自然有它的道理,试图穿山而过,一定是死路一条。
赵蘅大感挫绝,一筹莫展。千辛万苦才走到这里,难道说,真就走不了了么?
心灰意冷间,玉行忽然严肃地示意众人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