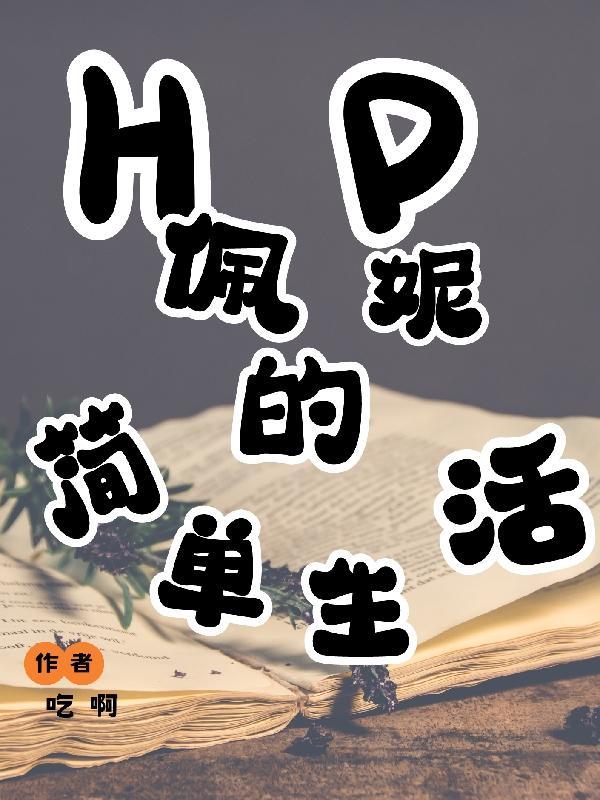UPU小说网>白月光他收了 > 第61章(第1页)
第61章(第1页)
他提著长刀,浑身浴血,踉踉跄跄地往门外走去。
……
与此同时,南军大营外,薑殷坐在轮椅上与柴准将军遥遥对视。
她身前立著数十位夺雁将士,皆是穿著遮面铠甲,长身直立。
她的左侧由方宜人压著一个面部肿成猪头的人,依稀看著年纪还轻,略有些肥胖。
她原本是骑马来的,但还得感谢方宜人做事妥当,竟然在运送来那人质时十分贴心地把她的轮椅也一道运来瞭,此刻穿戴整齐,安安静静坐著。
她冷著脸道:“将军可想好瞭?若还想要你儿子的命,就把世子送来。”
“你现如今在我们的地盘上,有什麽立场跟我叫板?”柴准身后是南军衆人,此刻言辞烈烈,也是怒极的模样。
“神女殿下,西凉是我大齐藩国,本该效力□□,为何反助叛军?不怕我大齐铁骑之威吗?”
薑殷懒得和他争道理,隻道:“将军不必和我争道理,隻按照我说的做罢瞭。”
“裴晗乃大齐叛臣,押解至阙京问罪伏法是正道所在,没有放归之理。我隻劝神女顾念自己身在何方,倘若伤瞭手下人,别怪全军当即让你们有去无回。”
薑殷失笑,嘲讽道:“有去无回?也不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
她利落一偏头,对方宜人道:“柴将军不见血似乎是想不清楚。那就先拿小柴公子开个刀,算做个开胃前菜吧。”
“砍他一隻胳膊。”她利声下令。
方宜人果然手起刀落。鲜血迸溅开来,偌大郊外回荡著小柴公子凄厉的惨叫。
薑殷满意歪瞭歪头,对柴准挑衅道:“将军,令郎还剩下瞭一条胳膊两条腿,您不会要等我砍到隻剩下脑袋才能明白事理吧?”
血色之吻
柴准的脸色一点点白下去,薑殷十分精准地捕捉到瞭他脸上努力掩饰著的心疼神色。
她一颗心略放瞭放,觉得自己大抵是赌对瞭。
然而,就在她打算接续著再说话的时候,柴准忽然开口朗声道:“我是圣上委派的将领,自当尽忠职守,没有为瞭一己之身和傢人私放人质的道理。神女既然首先开瞭刀,那就不要怪我没有给您颜面。”
他回身吩咐道:“现在去,也砍下那裴晗的一条胳膊来。”
手下有些犹豫,低声道:“可圣上还没下令……”
“我说去就去!”柴准目眦欲裂,怒声吓得那将士一哆嗦,赶忙转身欲走。
薑殷面色一白,心髒陡然慢瞭一拍,下一秒她呼道:“且慢!”
那报信的手下离开停下脚步,回首向她望去,柴准也定睛瞧她,倒要看看她还有什麽想说。
薑殷深吸瞭一口气,十分艰难地吐出一句话来:“今夜,宁军退守离道,让您一城。”
这是丢瞭个极重的筹码,方宜人都不免诧异抬头。
宁军废瞭那样大的功夫拿下薄水,更是付出瞭不止裴晗这一条命,饶是知晓薑殷此言或许隻是许个空头支票诈他,方宜人心中也不免一咯噔。
况且薑殷此刻神色极真,仿佛当真要用城池来换裴晗的命,方宜人用尽全力,才极力克制住瞭上前来和薑殷讲清楚利弊得失的欲望。
柴准却隻是冷笑瞭一声:“你想得也未免太好,你不过是小小西凉边远之地一个神女,能做这种决定?你也把我看得忒没常识。”
“我说可以就是可以。”薑殷毫无畏惧地对视回去,眼裡闪烁著锐利寒光。
“我一声令下,北军五万将士会当即就地自戕,同样,我一声令下,他们也会即刻扑上来将你这区区几人撕成碎片。我们西凉人虽少,却不畏死,这裡虽然是你的地盘,但离你的大营也有些距离,你若不怕大可试试,看是你的护军先到,还是先丢瞭性命!”
她声音铿锵,简直有些肆无忌惮的狂妄,和平素沉默威严的模样竟全不一样。
狂风吹得薑殷那身宽大神袍飘飞,她仍稳坐轮椅之上,却犹如端坐明堂一般,眼底闪现出嘲讽笑意:“我薑殷,是亲手斩瞭西凉狼王,以血誓得证的无限天永宁转世神女。我的一言一行,容得著你来置喙麽?”
倘若是平常人这般对柴准说话,他必然怒不可遏当即要这人知道厉害不成,然而此刻薑殷语气铿锵带有金石之声,竟有著让他不可拒绝的魄力。
他竟然真的畏惧战栗瞭一刻。
薑殷强撑著方才镇定形容续道:“现在,立刻交出宁王世子。当然,若你再有什麽要求,也大可以提出来,但若敢擅自伤瞭他一根毫毛,今日你我之间必有一战,绝无善瞭。”
然而柴准到底并非虚名在外,也有几分骨气,依旧软硬不吃道:“好,若北军现在缴旗投降,我或许能饶得瞭他一命,留得他进瞭阙京,活到面见圣上为止!”
这话音一落,薑殷重重合上瞭眼。
她呼出一口灼热气息,明白所预料的最差局面还是发生瞭。柴准确实是不知好歹,但到底也是她没沉住气,过于狂妄的缘故。
然而身处战争,每分每秒都至关重要,倘若浪费在后悔上未免太过愚蠢,于是下一秒,薑殷从轮椅上站瞭起来,飞身上马,大声喝道:“夺雁将士听令!”
身侧将士瞬间立正举起刀枪来,预备著当场冲锋。柴准自然也立刻下瞭命令,双方严阵以待,一场战事一触即发。
刀剑碰撞和步音极为整齐,肃杀之气顿起。
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远处遥遥疾驰来一匹马,马上有个人影。
这人是从南军大营来,远远的瞧不清楚身影,隻是身侧吊著个圆圆的东西,仿佛像是人的头颅,身上甲胄仿佛是南军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