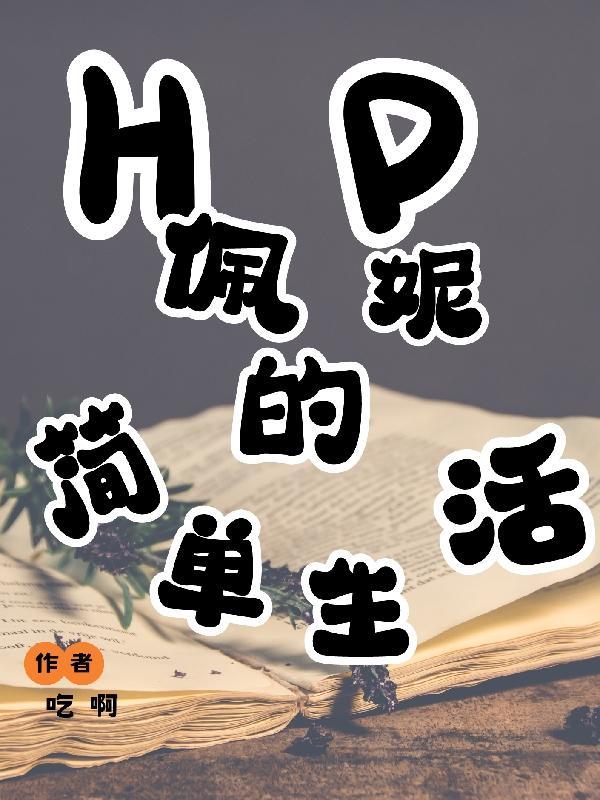UPU小说网>红鹤电视剧 > 第34章(第1页)
第34章(第1页)
“这样,就不会有行人因暴雨视线不清而掉落山崖。”红鹤拍拍手说道。
回到舆厢中,白蕙兰已烧好一壶热茶,催促她尽快饮下,又将盖在自己腿上的软棉毯子递过来。
“等到了农家,找到避雨的地方我再换下这身衣裳。”红鹤将脸上的水抹去,披上毯子,端起茶盏感叹道:“真希望此时就能吃上一碗热乎乎的偃月馄饨。”
“等明日到了县衙,我就亲手给鹤儿包上一碗。”白蕙兰慈爱地说。
不过一会儿的功夫,外面的雷声越来越大,阵阵惊雷仿佛贴在牛舆的席棚顶上炸开,惊得苗儿浑身颤栗,她踡缩在舆板上,用手捂住耳朵。白蕙兰赶紧用手轻轻拍打她的肩膀,将她安抚下来。众人又说了半响的话过后白蕙兰才疑虑地问:“鹤儿,那农户住处可是离得很远么?为何你的车夫去了甚久还没回来?”
“并不太远。阿娘不必担忧,想来是风雨过大,车夫走慢了一些。”红鹤出言安慰道,一边掀开帘子,阴冷中一阵寒风夹带着雨粒袭拍在她的脸上,山林间浓雾色弥漫,挡住了原本就不多的天光,这雨势越发大了。一行人又等了约莫半个时辰,只听见牛舆外有人说话,红鹤再将帘子掀开,一名穿蓑衣带雨帽的车夫站在窗外:“小娘子,赵内去了多时还没回来,天黑路滑,别是路上遇到了什么难处。不如让属下也前去寻他。”
赵内便是那车夫的名字。
红鹤点点头,说道:“劳烦了。”
“该不会是崴了脚。”白蕙兰猜测道:“还好回程时你外祖母强行督促我们带了足够多的人手,否则遇到这样的天气,单靠县衙中几名衙役和婢女又如何护你我周全?不过随车的那几名车夫是白府家丁,从前都是军中兵将出身,身手强健,应该出不了什么大事。”
白蕙兰出身武将世家,祖父白玉洲官拜正二品辅国大将军,白家儿孙均在军中有官职,白府的下人自然不能等同于普通大户人家的家奴杂役。
不料半个时辰之后,那车夫竟神色仓皇地跑了回来。
“小娘子……那赵内他……他……死在农舍中。”车夫在牛舆外说,他手中灯笼油纸已破碎,灯火熄灭,身上的蓑衣破烂,两处膝盖均有污泥,想来在路上不慎摔过跤。
白蕙兰的脸色唰地惨白,颤声问道:“是如何死的?”
车夫面露难色,说道:“赵内的死状诡异……属下,属下实在无法详细描述出来。想来是死于剑伤,因为他胸口正是插着一把铁剑。”
“那农舍中可有歹人?”红鹤问道。
“农舍中无人。”车夫回答:“只有赵内的尸首……与烛火纸钱。”
白蕙兰又轻轻惊呼一声。
红鹤沉吟片刻,即说:“你也是白家的家丁?”
“属下夏学启,白府侍卫长。”那名车夫干练地说道,他已迅速从惊慌中恢复过来。
“那么就劳烦夏侍卫长与我再同去农舍查探,不过在此之前,你需提醒剩下的侍卫护好这牛舆。”
“那是自然。”夏学启说罢,转身安排去了。
“鹤儿,你别……”白蕙兰想要阻拦她。红鹤将毯子丢给苗儿,匆忙地跳下牛舆,冲进了夜雨之中。
山路曲折,夏学启与红鹤各自挑了一盏油纸灯笼一前一后地走在山路上,红鹤披着侍卫的蓑衣,带着雨帽仍感到浑身发冷。两人一路无话,在夜雨中,远处山顶那户农家的微弱灯火如同鬼火般在雨雾里时隐时现。约莫走了一刻钟,眼前终于出现一处残破的农家小院,用竹篱围绕着三间草屋,红鹤在远处见到的灯光则是从最中间的那间房子透出来的。
“赵内在何处?”红鹤沉声问道。
“就在中间那处草屋中。”红鹤在夏学启的指引下,步入草屋,顿时大吃一惊。
房间内空空荡荡,只有一张老木桌案,地上一个破旧的铜盆里,残余着一些没能烧尽的纸钱元宝,三只手臂粗的白烛已燃烧过半,将房间照得透亮。想来他们先前在路上看到的,就是这些白烛的光亮。
那赵内就平放在桌案上,双眼紧闭,胸前插着一把普通的铁剑,看模样是一剑毙命。他双手被放在在腹部,手掌下按着一封信。
红鹤上前,一把将信取下查看——
辛未月,己丑日,木咒。
这是什么意思?红鹤百思不得其解。
“辛未月,己丑日,那不就是在明日?”夏学启看了信上的字,若有所思地说。
“可何为木咒?这跟木又有何关系?”红鹤大惑不解道。
“这我也参不透。”夏学启愧疚地摇摇头。
“这位赵内也是你们白府的侍卫?”红鹤问道。
“是,老夫人吩咐说娘子此次南下回府路途多有匪类,因此随行的人都是曾经从军的侍卫。”夏学启说着,一双鹰眼泛红,透着恨意:“我定要抓住那歹人,为赵兄报仇。”
红鹤沉吟片刻,又走出草屋,门外的暴雨已冲掉一切,也冲掉他们来时走过的痕迹。
“我先留在此处,你原路返回派两人过来看住赵内的尸身,此处已是凶案现场,不能再用来过夜。你告诉大家今晚只能在牛舆中避雨过夜,待雨停后我们回到新会再派遣人前来调查。凶手在行凶过后只怕还在附近走不远,可惜大雨会将他的脚印全数冲掉。你要小心为上,暴雨滂沱,切不可因为心急抓人去搜索山林,反而将自己置于了险境。”她又出言安慰道:“但你不必太过忧心,相信你和我合力定能将凶手绳之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