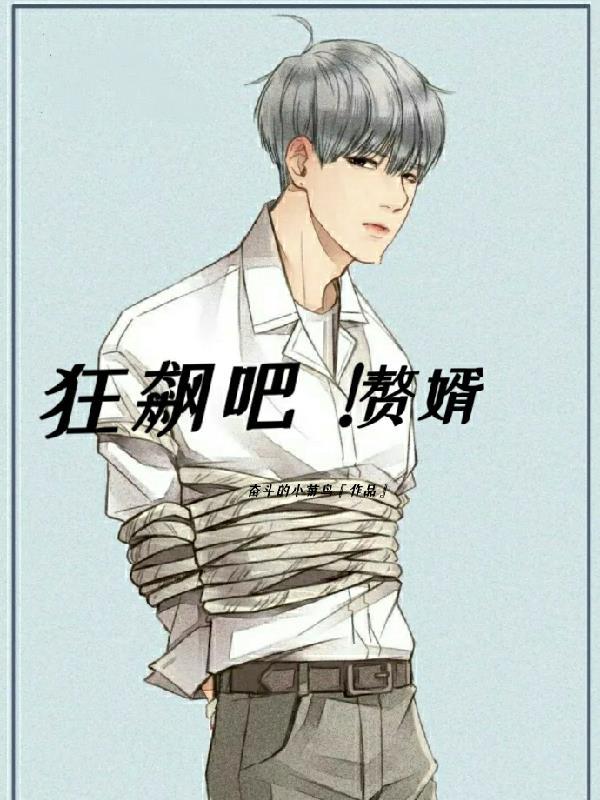UPU小说网>安陵容重生修仙 > 第124章(第1页)
第124章(第1页)
皇后听着皇上的呵斥,不住的摇着头,唇齿中溢出呜咽声,眼泪早就流满了整张脸。
“本该属于臣妾的福晋之位,被她人一朝夺去,本该属于臣妾儿子的太子之位,也要另属他人,臣妾夫君所有的宠爱都给了她,臣妾很想知足,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纯元是你的亲姐姐啊……”皇帝再也端不住了:“要你入府是朕错了。”
宜修跪的端正,目不转睛的盯着皇上:“皇上错在不是迎臣妾入府,是不该迎姐姐入府专宠姐姐,既生瑜何生亮啊。”
“皇上何等睿智,怎么到了自已身上就这样不明白。”
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她也不过是为了自保罢了。
皇上没接她的话,咒骂道:“你就不怕报应,午夜梦回的时候,你就不怕纯元和孩子来向你追魂索命!”
这句话却像是触动了皇后某根敏感的神经一般,她顾不得宫规体统,大声哭嚷着:“她要来索命尽管来索呀……”
死生不复相见
皇后隐忍多年终于爆发:“免得臣妾长夜漫漫,总梦见我的孩子向我啼哭不已。”
此时的皇上眼里充满了厌恶,愤怒和怨恨,唯独没有一丝同情。
当年,她的弘晖高烧不退,浑身滚烫滚烫的,却寻不到一个大夫,最后没了生息,她绝望的抱着死去的孩子,痛彻心扉的走在狂风暴雨下。
“孩子夭亡的时候,姐姐有了身孕,皇上你只顾姐姐有孕之喜,何曾还记得臣妾与你的孩子呢,他还不满三岁,高烧烧的浑身滚烫不治而死啊……”
“臣妾抱着他的尸身,在雨中坐了一晚上,想走到阎罗殿,求满殿神佛,要索命就索我的命,别索我儿子的命啊……”
“偏偏姐姐这时候竟然有了孩子,不是她的儿子索了我儿子的命吗!我怎能容忍她的儿子坐上太子之位呢!”
她在那晚的疾风骤雨中失去了自已的孩子,却被告知要去照顾刚刚怀孕的姐姐,她只能忍着丧子之痛,穿戴整齐的跪在姐姐脚下,恭祝她有孕之喜。
皇上眼里透出不耐烦:“你疯了!”
皇后一番痛彻心扉的哭诉,却只换来皇上如此凉薄的三个字。
他声声重音:“是朕执意要娶纯元,是朕执意要立他她为福晋,是朕与她有了孩子,你为什么不恨朕!”
皇上怒目圆睁,显然厌恶透了皇后。
“皇上以为臣妾不想吗?臣妾多想恨你啊,可是臣妾做不到……臣妾做不到啊!”
“皇上的眼中只有姐姐,皇上你可曾知道,臣妾对你的爱意,不比你对姐姐的少啊……皇上你以为姐姐爱你很多吗!”
她这样声嘶力竭的反问,反倒叫皇上的表情凝滞起来,当年纯元离世时候的叮嘱,却像是对家族的爱要胜于与他的夫妻之情。
“凡是深爱丈夫的女子,有谁愿意看见自已的丈夫与别的女子恩爱生子啊,臣妾做不到,臣妾做不到啊!”
养心殿帝后二人说些什么,安陵容并不好奇,她隐隐有预感,皇上今日必当废了皇后,只是当时太后去时留下的一道诏书,却是始终悬在安陵容心上的一把利刃。
孙竹息就像人间蒸发了一般,她费了许多人手去找,都没有踪迹。
养心殿,皇帝见皇后这副失心疯的样子,却更不想与她多说,起身拿起纸笔,开始写废后的诏书,正当他要盖印时,养心殿门口却出现了一个人影。
正是自从太后丧礼后便人间蒸发的孙竹息。
她手中还拿着一卷绢帛,进来后瞥见跪在地上形象全无的皇后,微不可察的叹了口气,便不再多看。
“奴婢漏夜前来参见皇上。”孙竹息垂首。
“孙姑姑,你怎么来了。”皇上闻言抬头,眼中有些惊讶。
“奴婢知道今天宫中有大变故,为免皇上烦心,特意带来太后遗诏。”
皇上放下手中印章,走上前去:“皇额娘有遗诏?”
孙竹息打开遗诏,见状皇上也跪了下去,与皇后并排。
“太后遗诏,哀家身后,皇后若有大不敬之罪,皇帝须谨记,乌拉那拉氏不可废后。”
孙竹息言罢,皇后闭了闭眼睛,有些安心的同时更多是悲凉。
皇上跪着接过遗诏,看了一番:“果真是皇额娘亲笔……”
皇后跪在那里,呢喃着当年封后诏书上的话:“兹尔福晋乌拉那拉氏,祥钟华胄……秀毓名门,温惠秉心,柔嘉表度,六行悉备,久昭淑德,于宫中四教弘宣,允合母仪于天下,曾奉皇太后慈命,以册宝册,立尔为皇后,钦哉……”
皇上在太后生前,便多有违逆,如今更不会听从遗诏,执意废后。
孙竹息声音敦肃:“皇上以仁孝治天下,不能不顾太后遗命,奴婢之所以未跟随太后到九泉之下,也是因为这封遗诏。”
“可是乌拉那拉氏之罪,不可饶恕。朕不能不废了她,以慰纯元在九泉之灵,还望在九泉之下的皇额娘恕罪。”皇上眸中带着怒火。
“太后临终前说过,若皇上执意废后,让奴婢问一问皇上,纯元皇后在临死前,伏在皇上膝上说的话,皇上还记得吗?”
孙竹息的这句话引出了皇上久远的记忆,他回忆似的呢喃着:“当时纯元已经奄奄一息,她伏在朕的膝头跟朕说,我命薄不能陪四郎白首偕老,连咱们的孩子也未能保住,我唯有宜修一个妹妹,望日后四郎能够无论如何都善待于她,不要废弃她……”
“是皇上亲口答应纯元皇后,决不废弃她的亲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