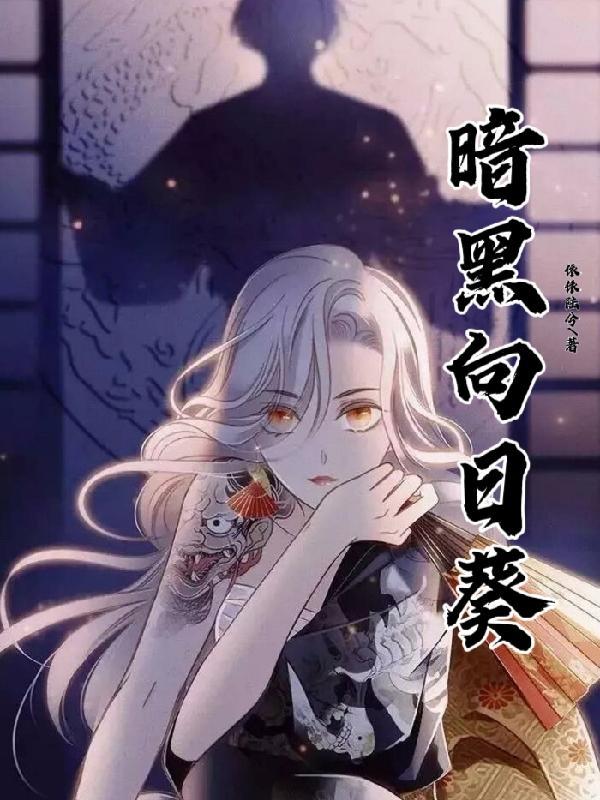UPU小说网>结爱.南岳北关 > 第33頁(第1页)
第33頁(第1页)
「沒事。」腹部的抓傷很痛,但皮皮保持鎮定。這不是她第一次受到祭司大人的傷害,四年前剛認識的時候,賀蘭觿就在一次爭吵中掐過她,算是發火時的習慣動作。
「謝天謝地,他沒咬我。」花青旗摸了摸頸子,心有餘悸,「身上要是有個天星族咬的洞,那就死定了。」
「不會,」皮皮立即辯護,「賀蘭觿不是這樣的人。」
「可憐的皮皮,」花青旗摸了摸她的臉,嘆了一聲,「你還是這麼無可救藥地喜歡著他,對嗎?」
「你以為他不知道你在演戲?」皮皮冷冷地看著她,不喜歡她裝腔作勢的樣子。
花青旗雙眉一挑:「當一部電影很感人的時候,你會流淚,是嗎?」
「……」
「儘管知道這不是真的,只是一群演員在攝影機面前背台詞?」
「……」
「賀蘭觿當然知道我不是慧顏,可他一看到我就立即入戲,攔都攔不住。」花青旗自信地甩了甩頭,將長發甩到背後。
就憑你這演技?皮皮在心底都快笑出聲來了:「那你還說他不愛慧顏?」
「受到刺激才能省悟。慧顏一死他的腦瓜就不轉了,心裡的鐘停罷了。需要有人給他當頭棒喝……」
「他什麼也不需要。」皮皮打斷她,「他很正常。」
「正常?他剛才的樣子正常?」花青旗的聲音忍不住高了一度,「皮皮你不是狐族,不明白我的能力。祭司大人需要治療,就像一個送進手術室的急診病人,你是家屬,我是醫生。你只能把他交給我,也只能相信我。治病救人是我的天職,我不會放棄這個使命。當他徹底痊癒的那一天,如果你們仍然相愛,我不反對你們在一起。實際上我不反對他跟任何一個女人在一起,只要這是一段嶄的戀愛,一段跟沈慧顏無關的感情。所以關皮皮,我再說一遍,讓醫生做醫生的工作,你是外行,不要參合進來。」
皮皮抱臂而視,一臉的不相信。
「他不僅是你的丈夫,而且是狐族的領袖。我這麼做不是為了你,或我自己。是為了整個狐族。」
她的聲音像一杯冰水從皮皮的耳朵一直灌進她的胃,令她打了一個寒噤。
「表演的事我不參合,」皮皮用目光鎖住她,「但他的魅珠是我的。」
「嗤」地一聲她笑了,搖了搖頭。
「不要跟我搶,」皮皮平靜地說,「否則送你回沉燃。」
說完這話,她又凝神了花青旗三秒,確信炸彈擊中目標,這才轉身向著篝火的方向走去。
沙灘上很熱鬧,細細的白沙上全是腳印。大家觥籌交錯,談興正濃,沒什麼人離開。
按照傳統,這樣的聚會都是通宵。
皮皮找了一圈,沒找到賀蘭觿。狐族聽力敏銳,皮皮的尖叫估計有不少人聽見,根據桑林私會之俗,此時有人尖叫也不奇怪。大家倒是對祭司大人的突然離席表示關心,紛紛過來問出了什麼事。皮皮腹傷疼痛,本來想溜,這個時候反倒不好意思走了。一面敷衍說賀蘭觿有緊急的公務要處理,先走一步,一面繼續跟前來要求賜福的人寒暄,穩住人心。過了一個小時,仍然不見祭司大人的身影,皮皮無奈,只得單槍匹馬繼續應酬。
花霖端著一杯啤酒過來問道:「賀蘭呢?」
「可能有事先走了,」在他面前,皮皮不好意思撒謊,「我沒找到他。」
「你們——」他停頓了一下,觀察她的表情,半開玩笑地說,「吵架了?」
皮皮看著他,不知道怎麼回答。她不清楚花霖與賀蘭的關係是否親近到可以談彼此的私事,決定保持沉默。
「我看見青旗身上有傷,特地過來問一下。」他試探著說,語氣很隨便,但皮皮能夠聽出他很介意。畢竟花青旗是他的妹妹,為了賀蘭在沉燃關了八百年,祭司大人可以生氣,可以發火,動手掐人就過份了。不看僧面看佛面,以花家在南嶽的地位以及這些年來對他的支持,他也不該如此衝動。
此時的皮皮真是尷尬之極。今晚本是年輕的帝展現王者風範的時刻,賀蘭觿又是遲到又是早退,對女人發火,還毆打自己的臣民,真是形象暴跌,丟人丟到家了。難怪他不肯露面,一定是羞愧到不行了吧?
「令妹演技高,令人神魂顛倒。賀蘭以為她是慧顏,隨即又意識到不是,就爆發了……這是他的軟肋,你懂的。」皮皮素有急智,越到緊要關頭越是對答如流,各種藉口信手拈來,邏輯上還沒有明顯的漏洞。
「我懂,」花霖的目光已化成了同情,「太懂了。幾百年過去了,他還是過不了這一關。」
「你覺得青旗……真能治好他?」皮皮問道。在她看來,這花青旗的演技也太不靠譜了。但狐族也有上千年的歷史,傳統中充斥著各種詭異的巫術,每個家族都有自己擅長的道法,就如當年千花的《十索》,真能治好也說不定。
「當然。」花霖顯得信心十足,「青旗從沒失敗過,你看——」
他挽起了袖子,伸出右臂,皮皮怔住。
上麵皮肉翻卷,凹凸不平,燒傷的疤痕覆蓋了整隻小臂,看上去慘不忍睹。
「我也有想不開的時候,當年曾經想燒死自己……」他的目色一片茫然,仿佛在尋找某種回憶,卻又怎麼也想不起來,「這不,現在活得好好的。我都不知道當年自己為什麼要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