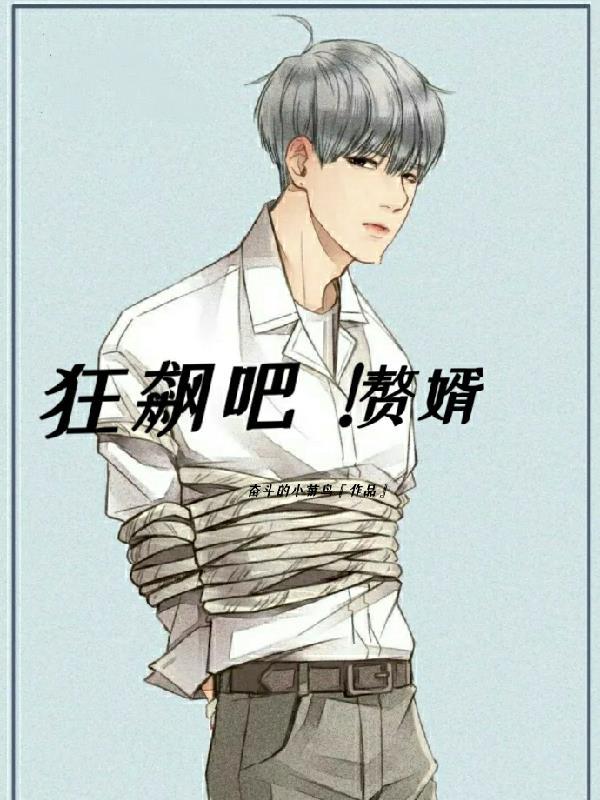UPU小说网>奈何明月照沟渠完整版 > 第62章(第2页)
第62章(第2页)
梁佩秋知道,王云仙让她去是为了给过去画上一个句号。如果这个句号始终不能画上,或许谁都无法好好开始。
她让趴在门边偷看的小孩拿了壶酒过来,狠狠灌了一大口才往后院角门走去。
稍后送客,那些个瓷行老板,船行主事都是安庆窑的重要主顾,王瑜定要亲自送去正门,徐稚柳若堵在那头也不好看,平白让人看了热闹不说,还丢王瑜的脸。
眼下以两家冰冻三尺的关系,王瑜没有直接让人把徐稚柳打出去,已是给了她这个寿星天大的面子。
梁佩秋见好就收,也不敢堂而皇之迎人进来喝杯水酒,只让小厮请他去角门,那里是日常采买送货专用的一道门,宽敞安静,也可以进出马车。
她走过去时,前方灯火耀目,徐稚柳已然到了。
他坐在车辕上,单膝曲起,手肘搁在上头把玩着一只捣药的兔儿爷,姿态闲适。
今晚乌夜沉沉,独他一人周遭亮如白昼,月萤蹁跹,画影重重,广寒宫的仙阁殿影仿若降临人间,而那高高的天上人,也纡尊降贵来了尘世间。
他只遥遥投来一瞥,梁佩秋就觉自己醉了。
她强打精神走上前去,学着王瑜和人寒暄时熟稔而虚伪的神态,勉强开口:“徐少东家,你的心意我收到了,这些东西还请带回去吧。”
她声音略显冷淡,也改了称呼,徐稚柳唇边原本就淡的笑意,在她开口后彻底消散。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她对自己如此冷淡。
他仍旧低头把玩物件,看似漫不经心,然不易察觉处手背却爆了青筋。
“就因你我立场相对,如今再见面就是仇人了?那我今日来送贺礼,可是给你添了麻烦?”他依旧温和有礼,带着一丝疏离。
梁佩秋道:“麻烦谈不上,只今晚有不少宾客在,恐怕会有非议。”
“非议?这不是你我之间最为稀松平常的吗?我倒不知,你在意这个。”一瞬间,他面沉如水,步步紧逼,“那你为何还来见我?”
梁佩秋不过三脚猫的功夫,哪里能敌得过修行千年的徐少东家,当头被堵了回去:“我只是、只是……”
早已打好的腹稿,一如那天他对自己说的绝情的话语,在这些天她已演练过数次,想着哪一日再见到他,就干干净净地回击过去。
这有什么难的?人就在眼前,快说呀!她这样告诉自己,偏又站不住脚。
原先她怕他等在正门被人看见,想亲自驱赶他走,可偏偏迎入了后院,像是不能见光的关系又蒙上一层薄纱。
本就让自己煎熬了,生怕说出口又次惹来误会,自作多情,自取其辱。
她努力地想,还有别的原因吗?想警告他,以后不要再来找她?可这话未免过于意气用事,日后她要管理窑务内外走动,少不得和他打交道,何必多此一举?
她想来想去,只是了半天也没说出个寅卯来。
徐稚柳脸上消失的笑又奇异地绽开。
梁佩秋被他这一声丝毫不加掩饰的溢出唇角的笑惹恼了,怒视他道:“那你为什么来这里?我的生辰和你有关吗?”
徐稚柳才要说什么,就听她追问道,“你不是已经和我划清界限了吗?不是要去追逐那片大好前途吗?不是连人命都不在惜了也要抢夺权势吗?还来找我干什么!”
看她一下子被逼得红了眼,徐稚柳到底于心不忍,翻下车辕,快步走到她身边,千言万语悬于一线,终化作一句:“小梁,对不起。”
仅仅一句话,梁佩秋强忍的泪水夺眶而出。
下一秒,被纳入温暖的胸膛。
她一时傻愣在原地,脑袋里嗡嗡作响,完全无法思考。而徐稚柳并不比她好到哪里去,虽则有怀疑,但他完全没想过在今晚试探,在一个不合时宜的时机试探,更不用说用这样一种冒昧失礼的方式来试探。
可不想梁佩秋因今晚王云仙或可表白而做了准备,男子外衣之下,是一件较为修身的女儿装。既做了女儿家装扮,就没必要再束胸,故而胸口软绵绵的一团,直接撞到了徐稚柳怀中。
那有别于男子的特殊的温软,电光火石间几乎烧光徐稚柳所有的理智。
他一点准备也没有,像是被雷劈中般,眼睛懵懵的,眨了眨,又似不敢置信,手臂环着梁佩秋微微抖,想再感受一下,又怕唐突到她,更怕是自己一时冲动,误会了什么。他就这么僵持着,保持着还没调整好的姿势,四肢逐渐麻木,意识却渐渐回笼。
梁佩秋也是一样。
两人久久失语,拥在一起,没有任何动作。
过了不知多久,徐稚柳先反应过来,极快地抚摸了下她后脑,将人放开,矮身平视着她的双眸,平复呼吸一字一句道:“小梁,再给我些时日,好吗?”
梁佩秋不懂这话的意思,情绪还停留在两人的别扭当中,一时转换不过来,身体是热的,脸是热的,心也是热的,但就是不想理会他,故而只是扭过头去,不敢看他。
徐稚柳也不勉强,牵了她的袖子到车辕旁,从里面拿出一只箱笼。打开箱笼,里面有她喜爱的酱猪蹄并几样小菜,还有一壶女儿红。
“今日是你的生辰,我怎会不来?原想着早点来的,可是……”大白天的若他出现在湖田窑门口,想必只会惹来更多的非议。
梁佩秋也猜到了他的意思,微微侧过身来。
徐稚柳低声哄她:“别生气了,都是我的错,上回是我说话太重,你大人有大量,不要同我计较,好吗?”
“那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