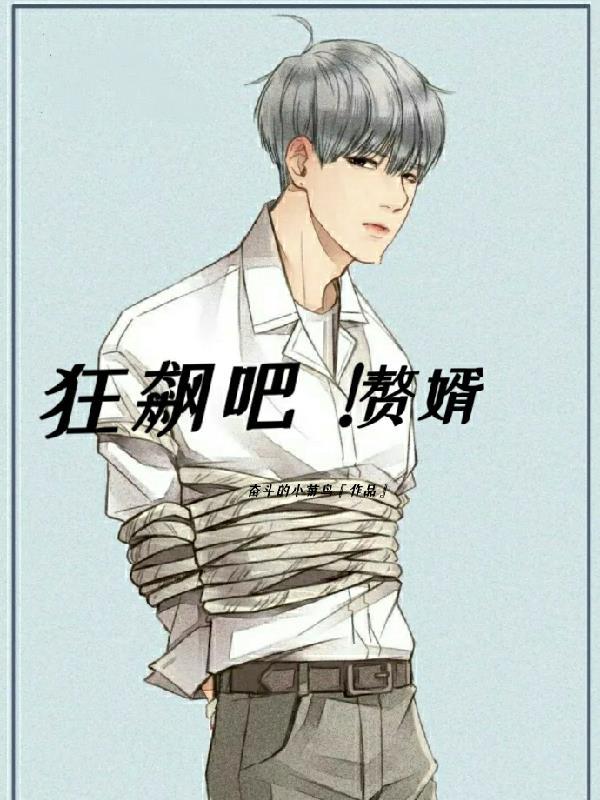UPU小说网>禁止说话的名言 > 第6頁(第2页)
第6頁(第2页)
他頭痛欲裂,腦中隱約可現昨夜發生的種種。散落一地的衣服和皺成一團的床單,也在提醒著霍成楓昨晚的情事有多激烈。
他有些煩躁地生出幾分自我厭棄:他怎麼能又跟符子縉……
他一把掀掉床上皺的不成樣子的床單,厭惡不已地丟到了地上,擰著眉轉身走出了臥室。
下了樓,還不等見到符子縉的人,他就聽到廚房那邊傳過來鍋碗瓢盆叮叮哐哐的聲音。
他愈加煩躁,快步走到廚房門口,想也不想就對著符子縉道:「你在幹什麼?」
符子縉被身後忽然傳出的聲音嚇得抖了一下,畏畏縮縮地轉過身來,「對,對不起,霍先生,我是不是吵到你了……」
他一抖,手腕便碰上了滾燙的碗壁,痛得縮了回來。
但他仍一聲不吭,只是用顫抖的手覆上燙紅的手腕,指尖使勁得掐入肉里,像是這樣就能用更大的痛感將燙傷掩蓋似的。
符子縉紅著眼圈,像只受驚的兔子。
他身上只掛了件襯衫,昨夜那場情事帶來的痕跡還未消去,星星點點,從外面裸露著的皮膚蔓延到襯衫的覆蓋之下。
腿根處更是一片青青紫紫觸目驚心,留下這些痕跡的人像是發狠泄憤似的,毫不留情。
霍成楓看著符子縉,像是被燙著了似的收回了視線。
這人總是這樣。
每天都做出一副柔弱可欺、純白無辜的受害者姿態——令他憎惡不已。
只有知曉符子縉的手段有多髒的人才明白,他漂亮的皮囊下,藏著的是一條吐著信子的毒蛇。
霍成楓還是認命地皺著眉頭,走過去奪下了符子縉手裡端著的東西,妥協似的道:「自己去上藥。」
於是他便看到,符子縉的眼睛裡即刻露出一股不尋常的、興奮的光芒來。
儘管霍成楓只是嘴皮子一動、輕輕巧巧地說了一句話,甚至沒有半分幫他上藥的意思,符子縉卻像是得了天大的恩賜似的,將方才喪氣的情緒一掃而空,歡天喜地地翻藥箱去了。
霍成楓心裡說不上是什麼滋味。
只要他看符子縉一眼,這人就能高興得渾身冒泡。
只要他對符子縉招招手,這人就會不顧一切地來到他所在的地方。
符子縉就是這麼的沒有底線,這麼沒有底線地喜歡他。
他的目光移向餐桌上擺著的、明顯沒有人動過的飯菜。
昨天傍晚,符子縉肯定早早地做好了飯、坐在空無一人的房子裡等著他回來,為了等他,從昨天午飯過後到現在定是一口飯都沒吃。
他等得鬱鬱寡歡,但是接到電話以後還是馬不停蹄地往酒吧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