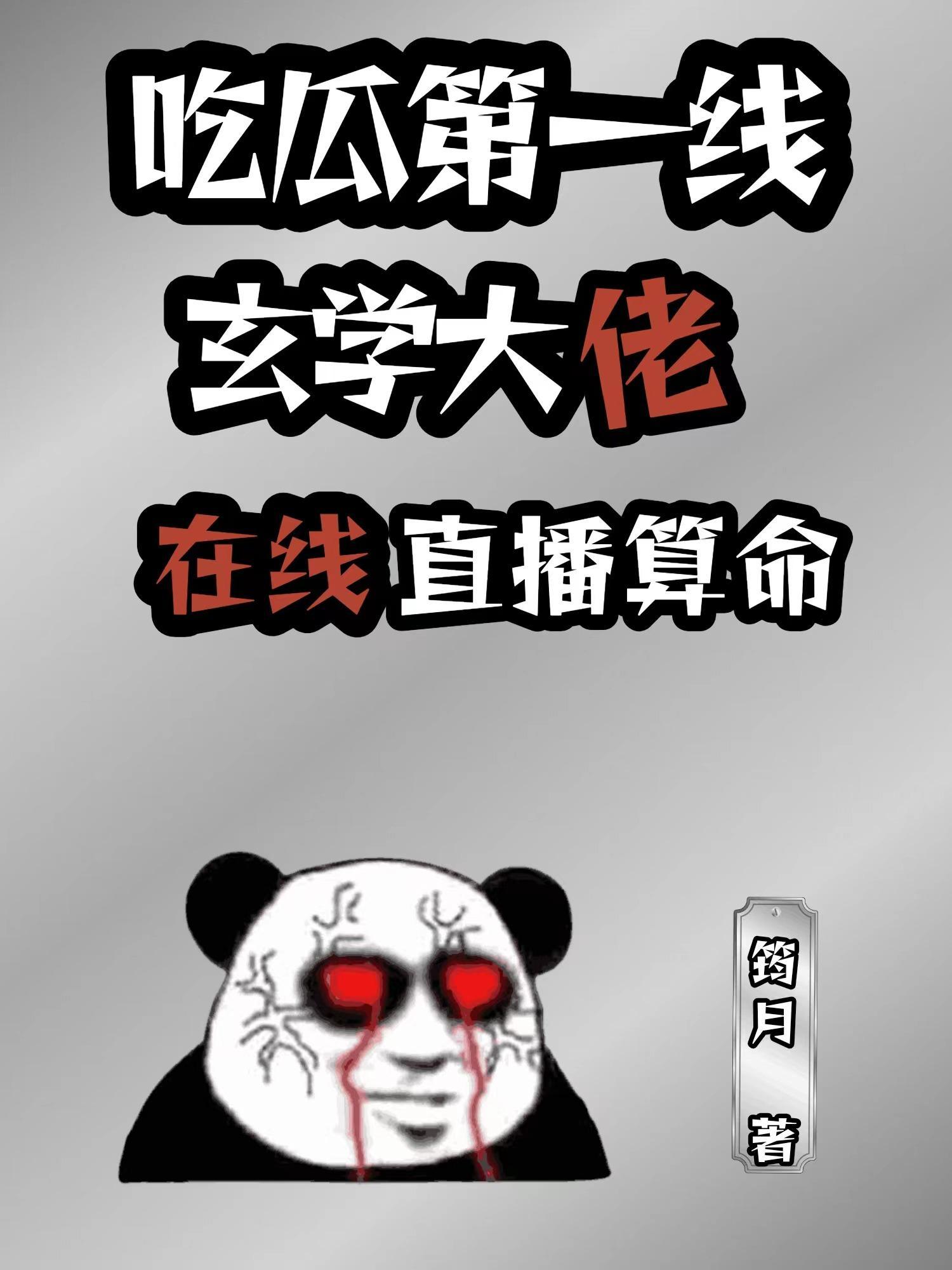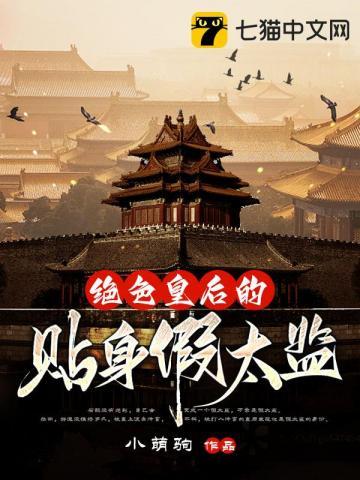UPU小说网>晗璐名字的意思是什么 > 第 7 章(第2页)
第 7 章(第2页)
盼夏在替她卸钗环,见她自回来后就是一副神色恹恹又唉声叹气的样子,那雀跃了半日的心里也没了底,不由小声地问及了今日的情况。
“公主是说,殿下早便看出来你是因为想去赴宴才去同他认错的?”
铜镜前的美人无力的点头,想到那推脱不了的事情就深感无力。
肖晗不愧是大燕的储君,只需一个眼神就能洞察她的内心,那拒绝的话还没说出口,他便已经猜到了她今日所为的目的:
“孤知道你心里在盘算什么,兜兜转转一大圈,不就是想去赴下月裴家的宴。”
“你便安心抄你的书,孤受不受这份礼,就看昭昭用不用心来抄了。”
这话乍然一听倒是没什么,可要细细品味,犹如平湖投石,能泛起丝丝涟漪,她可以粗浅的理解为,裴家的宴席肖晗带不带自己,取决于这赔礼和自己的态度能否让他满意。
话已至此,她也没了法子,既都到了这一步,左不过再熬几日的光景便可以随他出宫,她又有何不可的。
可直到离开的时候,肖晗也没给这件事下一个定论,换言之,她也不知道要抄到什么程度才能令他满意,而为了达到他的要求,她还不得不每日都去东宫,这种似是而非的感觉最是令人心里没底,又抓心挠肺般的难受。
她有些懊丧的垂头,心里是又气又恨,偏生这进退维谷的局面又是自己造成的,责怪了几个来回又绕回到了她身上,显得无趣又可笑。
第二日一早,修整了一夜的她早便收拾好了东西,这次她没有故意拖延和绕路,先是去了凤栖殿向皇后问过安后就直抵东宫。
肖晗已经去上早朝,殿内管事的就剩一个瞿恒,应是已经提前得了信儿,见到她来没有任何惊讶,同他的主子一般,淡漠着一张脸将朝露请进主殿。
一如往常,主殿内的陈设同之前无差,只是没了肖晗这个大冰块在,殿内温度都显得没那么冷。
和想象中的不同,本以为是要和他共处一室的,结果直到她将今日的字数写完,也不见肖晗出现。
瞿恒进来禀告,说他朝堂有事回不来,让朝露抄好了今日的便可离开,剩下的明日再来便可,这个结果她自然欣喜,没加思考的就收拾好东西离开了。
本以为那日只是例外,却不想仅仅只是开始。
从那之后,她每日就像例行公事般的去到东宫抄书册,日出而至,日息而离,而肖晗这些日子来不知在忙什么,两人压根就没再见过面。
可眼看着时间愈发近了,她心下不禁着急起来,这日抄完过后,有些忍不住朝瞿恒问道:
“瞿总管,皇兄可有说今日几时回来?”
瞿恒不似卢绪,性格要持稳的多,面对朝露的疑问,他的回答就像他这个人一样,分寸有礼且滴水不漏:
“主子的事奴才也不知,只殿下之前只会过,公主每日里做的事情他都知道,答应过公主的话也都记得,公主只耐心做好自己的事便好,旁的,殿下都心里有数。”
话已至此,朝露也不便多问,也只能满腹心事的照旧而为。
裴家即将办大事,有心思巴结奉承的人早已在奔走,皇城内廷早已互通宫外,就连宫里最末等的洒扫宫人都知道裴家的嫡子已经回了。
朝露这些日子以来都奔走在东宫和凤栖殿之间,一门心思都放在了别处,对这类消息的获知自然迟于众人,等到终于知道时,已经到了裴家快要开宴的时间。
这日,她照旧先来凤栖殿请安,近些日子,她每日都去东宫誊抄书册的事情在宫内已经不是秘密,一来二去就连皇伯母也听说了,她也没有避讳,请安时也将要用的东西给捎带上。
可今日来请安不似以往,皇后见到她时是一脸的惊讶,就像她今日不该再出现这里一般:
“你怎的今日都还要去东宫?”
她被问的满脸懵懂,像一头误闯无知领域的小兽:
“皇兄没说让我今日不去,可是发生了什么事?”
“太子没告诉你,明儿要去裴家赴宴,你这会不准备明日要用的东西,怎还在往东宫去?”
皇后是裴家人,说话自然向着母家,沉吟的音色配上疑问的语气,是在责怪她的不懂事无疑了。
肖晗让她用抄书来交换出宫的机会,却直到今天都没能给她一个确定的答复,以致皇后以为她轻慢裴家,言语之中多有怪责。
她满腹心事的出了凤栖宫,脚步却依旧往东宫而去,今日的天色不好,盛夏里头的灰蒙蒙色,是要落雨的征兆,就像她此刻的心情,沉闷不已。
瞿恒还是一如既往的迎了她进殿,恪守着他骨子里的规矩,不多问,亦不多言。
她也没什么要说的,强迫自己潋下心神后就开始了今日的誊抄,说来也巧,明日是裴家开宴的日子,她誊抄的内容到今天为止不多不少,正好抄完。
但可惜的是,直到最后离开东宫,也不见肖晗回来,亦没听见瞿恒有什么话要交代。
回朝阳殿的路上,灰暗的天空响了几声闷雷,瞧着,是真的要下雨了,声音一出,树梢上的鸟儿被惊的以作四散,她抬眸望去,忽而羡慕起那些鸟儿来。
比起自己,它们至少是自由的,能随心所欲决定自己的去留,总好过寄人篱下,连一个简单的诉求都要看人脸色行事。
鼻尖上有水珠落下,夏夜的雨说来就来,她抱紧了怀中的东西,足尖轻点的就往朝阳殿去。
在东宫等了一日没有结果,还因为这事被皇后责怪,对于明日的筵席她已不报任何希望,有些丧气的步入朝阳殿。
却在刚入主殿大门的时候,听见盼夏兴奋的声音:
“公主再不回来奴婢就要亲自去寻你了,殿下方才派人把你明日要穿的衣物都送来了,还让人传话,明日辰时过后他亲自来接你去裴家赴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