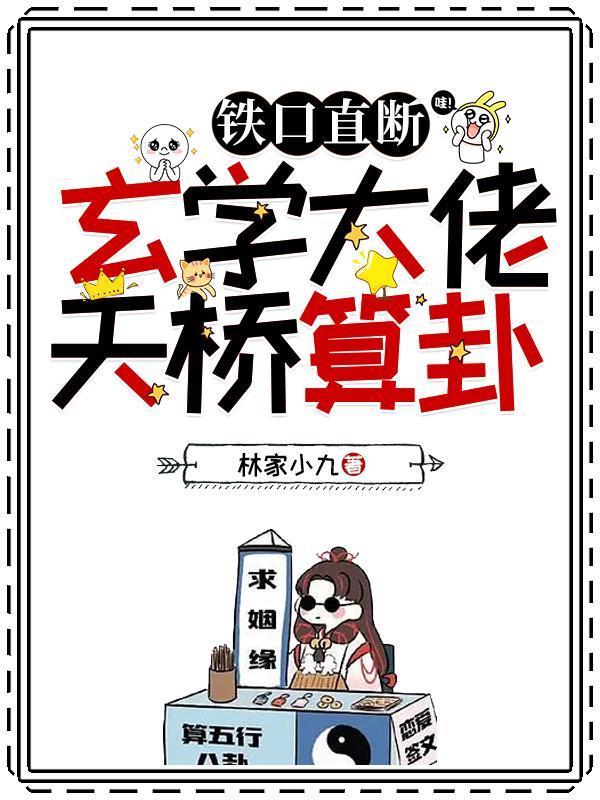UPU小说网>白月光分手有你才相信他的好 > 第179章 控制狂(第1页)
第179章 控制狂(第1页)
在贺时卿以前出国留学的那两年里,他曾无数次找过伊斯特大学的心理辅导师约翰,这位年纪不大的白皮肤男人一度成为贺时卿那两年里对话次数最多的对象。
面对这样一个人身处异国他乡,又不太乐意主动合群交朋友的年轻男孩儿,约翰先生见得太多了。他知道这类男孩儿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家里有钱有地位,对庸俗的感情缺少共鸣,或者现阶段的人生正处于迷茫与自由的拉扯期。
贺时卿看上去也是如此。
来这所学校就读的学生要么非富即贵,要么成绩优异,因此能给这位年轻医生留下深刻印象的其实并不多,但没想到贺时卿却是其中一个例外,因为当时这位年仅十九岁的男孩儿第一次见面就问了他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
如何才能把一个人控制在自己手里。
约翰医生当时直接给贺时卿做了一项性格测试,结果为d型人格,也就是俗称的,内心有潜在的控制欲存在,时强时弱,时好时坏。
贺时卿的反应不出意料的有些不乐意,毕竟“控制狂”三个字,绝大数都会跟电视上的法治频道相关联,恰好这位心理辅导师做出的结论也委婉,他告诉贺时卿,压制住自己的欲望,就不会犯错。
这句话并没有深刻的长存在贺时卿的潜意识里,但他从那一天起再没有说过任何诸如此类奇怪的话。仿佛随着时间的累积,这份欲念在慢慢消失,他成长为了一切都唾手可得的小贺总,风光无限,爱恨自由。
可终究只有他自己清楚,到底是压抑还是消失,不屑或是没到他动用这份欲念的资格,亦或是正如那一天所痛快倾诉的那番,他不过是在做一场精心的准备,只为和那个人重逢。
阮柠最后如愿的走进了他的生活里。此后,扎根的欲望便开始芽、生长,一步步灌溉茂盛到如今。
或许从阮柠第一次孤身去图书馆时,他就有机会阻止自己的,给她自由,给彼此一点空间。
但贺时卿在图书馆楼下待了整整两个小时,都没有成全自己,和楼上的人。
每一次抱有目的的通话,每一次看上去有些诡异的巧合,贺时卿都希望阮柠能早点现,又希望她永远都不知道。
因为到此刻,他都还觉得,他留不住她,她没有多爱他。
所以,即便到这一刻,当阮柠现端倪对他出质问的时候,贺时卿都还是泰然自若地撒谎道,“没有吗?我记得吃饭的时候你聊过啊。”
见男人笑得很从容,阮柠轻微皱了皱眉,她欲言又止,呢喃的话是说给自己听,“有吗……”
贺时卿捏了捏她的耳垂,亲昵地答道,“傻瓜。”
阮柠觉得有些奇怪,但又说不上哪里奇怪。她没再观察贺时卿的反应,而是自己先下了车,走在前面若有所思。
贺时卿也随她一起往房子里走,他没有干扰阮柠此刻还残存的疑问,只是步子似乎越来越沉,但脸上依旧挂着没有破绽的淡淡微笑。
等两人前后停在玄关,他先脱了鞋,身边的阮柠才终于动了动,转回身来看向他。阮柠的表情变得凝重起来,明亮的眸子直白的盯住面前的男人,然后她再一次肯定地说道:“你骗我,我没有说过,全程我只参与过三件事的聊天,其中两件是6海上次逛街买的衣服,另一件是温明轩聊到了孙希瑞,我跟着问了一些情况而已。”
她的表情很是难堪,补充了一句,“我不是非要这么认真,但你在骗我。”
气氛凝滞了片刻,贺时卿最终叹出了一口气,没有正面回答她,而是唤她的名字。
“阮柠。”
阮柠咬紧了嘴唇,没有对这声呼唤做出回应,而依旧紧紧盯着对方,脸上的表情变得复杂起来,有惊愕,也有失落。
他把阮柠的一切神情看在眼里,只好开口承认道,“对,你没有说过。”
他一说完,阮柠连鞋也不换,直接掉头往客厅里走,背影气势汹汹。
贺时卿慢慢地往里走,看见阮柠已经双手抱胸,一脸阴沉地注视前方不语。
贺时卿走过去,故意走到阮柠面前,手刚伸到一半对方就知道他想干嘛,于是阮柠直接将头扭向别处。
贺时卿没有恼,他知道自己理亏,可又始终无法开口解释这一切,他就一直站在她面前,居高临下,但表情又十分无辜忠诚。
两个人就一直这么僵持着,直到过了很久,贺时卿看到阮柠酝酿好一会儿才重新偏过头来,此时眼眶却已经红了大片。
贺时卿这下慌了,他赶忙蹲下来,像只讨好的小狗一样歪头去看阮柠,然后轻言细语地说:“宝宝,我错了,别难过。”
阮柠紧咬住下嘴唇,等到无法忽视对方不断追寻而来的目光后,她才问:“你在监视我,还是跟踪我?”
贺时卿苦笑道,“想什么呢,今天只是刚好找Jeffrey问了下你在哪里而已。”
阮柠并没有哭,她只是有点难过,这点难过刚好可以掩饰掉她的恐惧,她的眼睛虽流不出东西,但却湿润一片,亮晶晶的,这样盯着人看时,总会有种这世界上最单薄的干净藏在里面。
所以贺时卿不自觉地顿了一下,他又说:“你给我打完电话以后,我还是打算让Jeffrey送你的,但他告诉我你没在家,我才让他去找,然后他就告诉了我你在木柳街。”
阮柠心乱如麻,她忍不住又问,“那他怎么就知道我在那里?”
这种怀疑的因子一旦被打开,后果就只有无休无止,贺时卿也微不可闻的蹙了一秒眉头,但他很快又哄道,“木柳街那边出了车祸,可能是直觉吧,他就过去看了一下。”
这些解释看起来都毫无破绽,阮柠僵硬住的背脊也终于放松了一点,她一开始只是猜到对方有可能在监视或者跟踪,心里头翻涌的害怕铺天盖地地涌来,可贺时卿又回答她只是凑巧,只是运气。
贺时卿充满蛊惑和自信的话又充斥进耳朵,“你不信的话我把他喊来就是了。”
这种事非要拉上外人来讨是非说法的话,阮柠也会觉得是自己太过钻牛角尖,于是她赶忙喊住贺时卿打电话的动作,“不!不用,算了。”
她一时捋不清思绪,胸腔里的生气也随之消散不少,只剩一点儿懊恼残存,使她低着头呆呆的看着地面。沉默良久,这时突然换作贺时卿开口了。
男人一直以谦卑的姿态半蹲在她面前,他一只手抚上阮柠的脸颊,见到对方没有再逃避,他才安心地微微一笑,然后问道:“那么,你可以告诉我,你今天去那里做什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