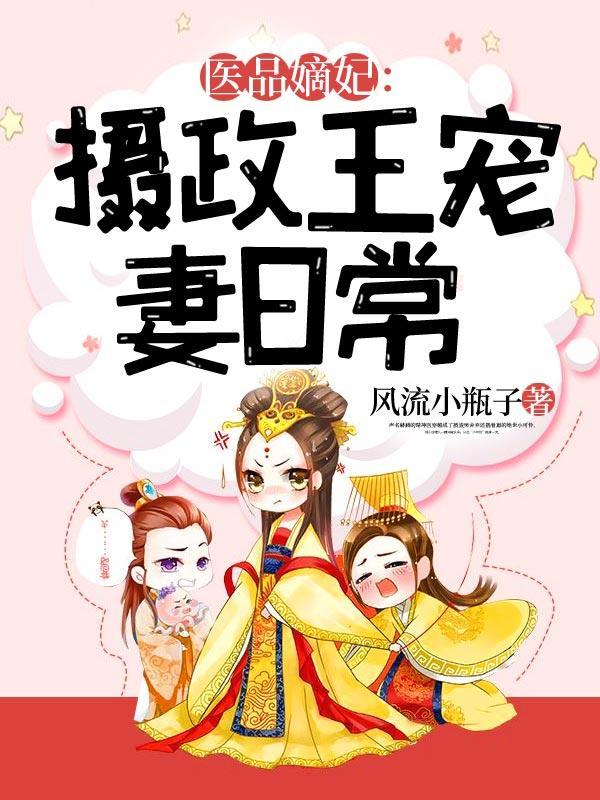UPU小说网>疯心难救by海苔卷第五章在线阅读 > 第91页(第1页)
第91页(第1页)
三室一厅,看着很空。家具都拿白布盖着,镜子电视这种能反光的也都贴着白纸。
傻强打开窗户通风,丁凯复四下打量。两个卧室的门都没关,一眼就能看出哪个是孩子的。
房间布置得用心。木质的上床下桌,通往床铺的台阶被做成收纳柜,彩绘着蓝色小鲸鱼。桌面摆着大背头电脑,桌下插着小转椅。
靠墙是一面书柜,塞得满满当当。从十万个为什么到世界地理,英雄人物故事,国内外名著,日本的黑白漫画。最显眼的是一套精装的演义,这种硬壳书在当年要好几百。
九十年代初期就能给配电脑用,还买这么多书,看得出这家人对孩子很是宠爱珍视。
余远洲的童年,无疑是幸福的。他的父母很爱他。
在意识到这一点的瞬间,丁凯复终于懂了什么叫「后悔」。不是后悔巧合,不是「凶手是他就真倒霉,不是他就oJBk」的那种后悔。
而是后悔伤害。他剥夺了余远洲本该幸福的童年,他让幼年的余远洲哭泣。这让他感到心痛,后悔。
其实如果余光林不是余远洲的父亲,他断然不会反省这段罪过。
在这世界上的某个人,童年比他幸福百倍,然后被他不经意给毁了。
别说后悔,他都能呵呵乐,然后把这事儿就白酒喝。什么余光林余暗林,惹了他,那就活该变成余永别。他才不会觉得愧疚难过呢。
丁凯复这种极度的冷漠,可能有一部分是天生,但大部分源于他的幼年经历。
一个没被无条件爱过的人,是不会有悲悯之心的;一个没被社会保护过的人,是不会对社会有责任感的。
世间于他无恩,他亦对世间无情。
但他对余远洲有情。
只有余远洲的痛,才能痛到他身上。他也因此才能从这份痛中明白,伤害到底是什么。
丁凯复弯腰钻到床下,缩到小转椅上。环视一圈,拉开了抽屉。里面躺着个变形金刚,下面压着个大信封。
他把变形金刚拿出来,摩挲了半晌。这是那张全家福上的变形金刚。
每一个8o9o后的男孩子,要说童年最想要的礼物,估计就是变形金刚了。这部日本动漫刚引入国内,就燃遍大江南北。
丁凯复肯定是没看过的。饭都吃不饱,哪有条件看电视。但即便如此,他也知道这个玩意儿叫变形金刚。实在是因为当年太火了。火到什么程度呢,但凡是个机器人模样的,也不管能不能变形,一律都叫变形金刚。
这么多年过去,玩具的塑料还是亮到反光,连明显的划痕都没有。
幼年的余远洲,一定是万分宝贝这个东西。
他会把它举起来,嘴里gigigi地给它配音,在这个家里快乐地跑;会把它搂在枕头边上,睡觉都给盖一半被子;会把它放到重要的东西附近,让它充当保护神。
多么绚烂幸福的童年,多么天真可爱的余远洲。
这么想着,他又抽出那个a4复印纸粘的信封。
信封上孩子的触写着:十二周年。以后妈妈不要骂爸爸了。
里面是一张结婚证,被撕得稀烂,又被用透明胶一点点粘上。
八十年代的结婚证还不是本子。软厚的红纸,贴着两张黑白照。撕得很碎,连照片都没能幸免。足以看得出撕证的人心中有多怨,多恨。
而能把这么一张碎纸机搅过似的东西按照原样拼好,应当是花了不少时间和功夫。
不管是撕证的人,还是拼证的人,皆是揣着一颗血淋淋的心。
丁凯复这种敏锐度的人,从来不需要有人把话完整地告诉他,他已经能猜出来个七八。
撕结婚证这种事,男人是不会做的。因为没用。要离婚,就去民政局。这种“刀子嘴豆腐心”的无用功,大抵只有女人才干。
而拼证的人就更好猜了,在谁抽屉里谁拼的。再往细了想,结婚日期1986年,结婚12周年就是1998年。正好是17年前,余光林自杀那一年。那因为什么夫妻不合,已经不用猜了。
丁凯复把结婚证小心地塞回信封,唤道:“傻强。”
傻强屁颠屁颠地凑了上来:“哎,枭哥。”
“往后,我想去做个好人。”他冷不丁地道。
傻强被这突然的立地成佛给整懵了,啊了一声:“枭哥本来就是好人。”
“我说的好人,不是对你好的人。”他食指钻头似的戳着傻强的肩膀,“是那种傻B。”
丁凯复用指头钻人这个动作,通常表明他心里不痛快,但他在克制。
傻强被钻得龇牙咧嘴也不敢躲,讨好着拍马屁:“枭哥想做什么,我都配合。”
丁凯复收回手指,站起身从四四方方的窗户往外望。
“好人。呵。好人。要么是纯傻B,要么是想装B。你这么觉得吧。”
傻强捂着被钻疼的肩膀,干巴巴地笑了声。
丁凯复也不是要他的回应,自顾自地接着道:“我原来也这么觉得。”
丁凯复这辈子,想做过很多种人。做牛人,做狠人。做有钱人,做人上人。但他从没想过做好人。
因为在他的眼里,「好」是没有价值的。「强」才有价值。
只有强者才能活下去,只有强者才配活下去。
人心,尊严,权利,感情。这世上没什么不能交换买卖。人可以做一些牺牲,但那必须是为了拿到筹码。然后用筹码去换自己想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