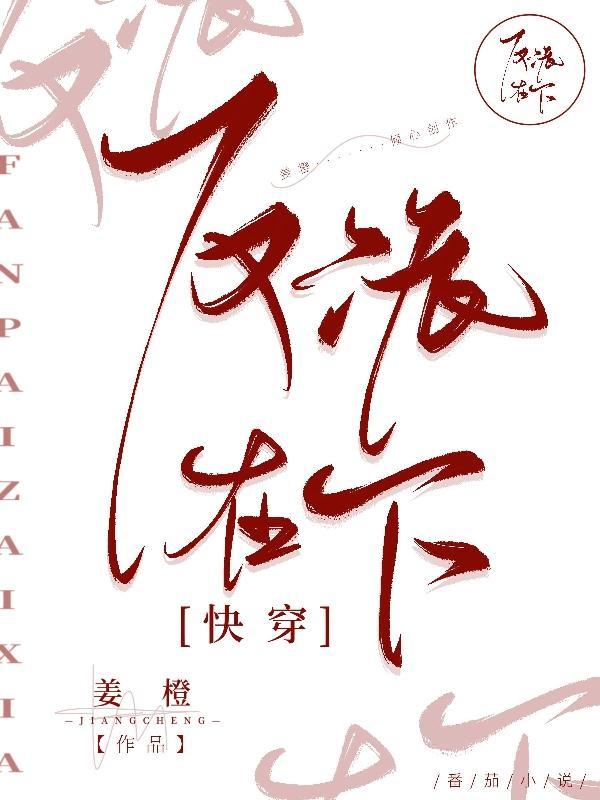UPU小说网>浮生之刃免费阅读 > 第4章 迷途 第十回 初识红颜(第1页)
第4章 迷途 第十回 初识红颜(第1页)
做完头疗,女孩柔声说:“先生,你把身子转过去,我给你做足疗。”
傅士雷顺从地转过身去,把双手架在脖子底下,头微微往上抬了抬,看着正在专注地做足疗的女孩,那是一张纯净的面庞,没有施过任何脂粉,就像一支刚刚出水的芙蓉,是那么清新自然,鼻翼上微微渗出的细密汗珠,就像雨露一样,点缀在优雅的花瓣上。她的一双手正熟练地游走在傅士雷的左脚上,或按或揉或捏或捶或搓,让人受用不已。手到之处,她的双眼也非常专注,仿佛她面对的不是脚,而是艺术品,需要匠心独运的精雕细琢才能趋于完美。
傅士雷情不自禁地赞美道:“你很敬业,按摩水平也不错。”
“谢谢夸奖,只要你满意就好。”女孩并没有抬头,只是浅浅地一笑,嘴边立刻出现两个圆圆的酒窝儿。
“不是我夸你,是你确实不错。”傅士雷见她仍不抬头,就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三十二号。”
“我问你的真实姓名。”
“我们这里都说号,号就代表人。”
“如果我想知道你的真实姓名,你能告诉我吗?”
“能啊,我叫梁思燕。”
“梁思燕。”傅士雷念叨了一遍,“这名字挺好听,谁给你起的?”
“我爸起的,我还没出生他就给我起了。”梁思燕的脸上溢满了幸福。
“你不是在骗我吧?这个名字只适合女孩,如果你生出来是个男孩怎么办?”
“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我爸说都叫思燕。”
“为什么非叫这个名字?”
“因为他和我妈的感情很好,我妈的乳名叫‘小燕’,所以第一个孩子必须叫思燕……瞧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梁思燕的脸上泛起一片绯红。
看着那娇羞的模样,傅士雷有些呆了,他没想到在这种地方竟然还有这样单纯的女孩。他怕梁思燕太尴尬,就把话题一转:“你爸是不是很有学问?”
“没有多少学问,就是在家种地的农民。”
一听梁思燕家里是农村的,傅士雷又对她增加了一分好感,便问道:“那你家里是不是很和睦?”
“那当然了。”梁思燕双手的动作没停,稍稍抬起头,看着傅士雷反问道:“那你家里呢?”
那是一双清澈无比的眼睛,没有任何世俗的东西在里面。傅士雷本来想说自己的家庭不和睦,但又一想,何必把自己的烦恼说给人家呢,于是他挤出一丝笑容说:“我家里也挺好。”
“我猜你家里就挺好。”梁思燕低下头去,继续做足疗。
“哦?你是怎么猜的?”
“因为你是个好人,所以家庭就应该好。”
“你怎么知道我是好人?”傅士雷的好感开始动摇了,“你们这些人太爱说奉承话,是不是你们在外面待的时间长了,专拣客人爱听的话说?”
“你不信我的话?你说我在奉承你?我可不是那种人。”
“那你是怎么知道我是好人的?之前我没跟你说过话,甚至连看都没看过你。”
“我当然有理由了。你每次来这儿,要么像以前一样一直在睡觉,要么像今天这样,跟我聊聊家庭情况。而别的客人,要么问我陪不陪睡,要么就讲一些乌七八糟、不堪入耳的黄段子,甚至有的还假装喝醉酒对我动手动脚。这样一比较,你不就是一个好人吗?你刚才和我说了那么多话,连一个脏字都没有,所以我断定你就是一个好人。”梁思燕不疾不徐地说。
“听你这么说倒是有一些道理,我刚才错怪你了。不过,你每天接触好几个客人,我又这么长时间没来,你怎么会记得我?”
“当然记得了,来了两次都是倒头便睡,而且一睡就怎么喊都不醒,害得我做足疗时要用很大力气才能把你转过去。”梁思燕抿嘴一笑,仿佛梨花初开。
傅士雷觉得这个女孩与众不同,她全身上下似乎有一种吸引人的魔力,让人既亲近又不敢有丝毫的亵渎。
梁思燕说,她的家在南方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那里非常穷,她是家里的老大,下边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本来梁思燕有上大学的机会,可是家里太穷,实在供不起她。于是她把心一横,高中一毕业就辍学务农,帮父母干些杂活儿,一心一意供弟弟妹妹考学。可是在家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也挣不到几个钱,等弟弟考上大学,经济上依旧捉襟见肘,根本拿不出那么多学费。没办法,只能靠借。为了还债,梁思燕不得不出来打工,本来想找一个工地做些杂活儿,可是一个女孩家,走了好几个工地人家都不收,最后还是一个做足疗的老乡把她带到这里。刚来大富豪的时候,看到这里干什么营生的都有,甚至有些小姐干那些肮脏污秽的人肉生意,吓得她赶紧往外跑,但是那个老乡告诉她,在这里做什么全凭自愿,如果不愿意做小姐,做按摩也可以赚钱,只是赚得少些,但不用出卖肉体,她这才答应留下来。做了这几年,也习惯了,虽然有时看到的听到的尽是一些让人不堪的东西,她只当是影视剧里的情节,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她曾无数次地告诫自己:只要心里平静如水,就不会横生波澜。
听着她的经历,傅士雷感慨不已。看来每个人活得都不容易,都在为自己或大或小的理想而时刻不停地奔波在人生的道路上。他非常佩服梁思燕,这么一个弱女子,背井离乡,为了供弟弟妹妹上学,为了奉养父母,不惜忍辱负重,一力承担,而且还能洁身自好,不被世俗所染,真是难能可贵。想想自己,虽然手捧铁饭碗,却不如梁思燕这般坚持如一,真是惭愧不已。
从大富豪出来,傅士雷看着满天的繁星,感觉清凉如水,但一想到自己有家不想回,有妻不愿见,烦闷之情便又充塞心头。看看已是十点多钟,估计曹立娟已经睡着了,他这才决定回家。
他轻轻地打开家门,蹑手蹑脚地进了卧室,正暗自庆幸平安无事的时候,突然一个枕头飞过来,随之而来的是曹立娟的喝骂:“你还回来干什么,有本事你就别回来,死在外头得了!”
傅士雷愣了愣,喘了几口粗气,平息一下愤怒的心情,扯了条被子,到客厅的沙上睡了一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