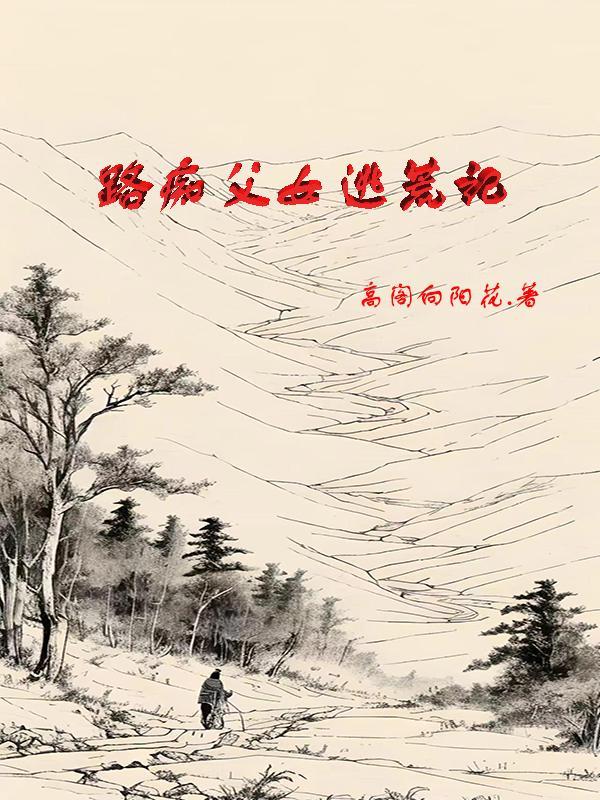UPU小说网>乙女好感度 > 第88章(第1页)
第88章(第1页)
房间内寂静了许久,空气像是粘稠的液化,女子似是无法将那一句句胆大妄为、难以启齿的言语诉诸于口。
“梦里的我,像是失去了伦理与道德的束缚,那些只敢在心中想着的事情,不知怎的就都轻易做了出来。”在教皇看不到的角度,阮姝娅神情放松,丝毫不见半分心虚愧意。
女子的声音中带着纯粹的信任,与第一次相比,她显得不再那样拘谨,能够更好的倾诉出心中的感受,“我…我在梦中的性格,似乎格外恶劣,我平时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也知道,我不应该做那些事。可…我看到他时,就忍不住想要见到他失态的模样,想要欺负他,想要他露出只有我能够看到的表情,想要让他在我的面前哭出来。”
“我知道,这是错的,现实中的我从不敢对他有任何僭越之举,即便有亲近之心也会克制着不去做任何撒娇亲昵的情态。”
梦境过于真实,模糊了与现实之间的界限,樊鵺却记得很清晰,那些颠倒的、令人恐慌的、动摇心神的一切都仅仅存在于夜里的梦中。实际上,圣女的确不曾显露出任何出格过分的狎呢行为。
教皇觉得他似乎也病了,像是被邪魔侵入了内心,竟然鬼使神差的想要问她,她梦到了什么。
是不是,那些夜里令他自愧、自责、自恼,让他像是被剥光了外皮暴露出可怖丑陋的连自己都不知晓的另一幅面目的人,其实就是她。
人的梦境能够在不知情的时候相通吗。
樊鵺像是被架在火焰之上受着灼烧之刑,他的确在犯戒,还卑劣的猜测是女子入了他的梦中,妄图将错误归咎于圣女的身上。
他犹如赤o的行走在沙漠之中,皮肤寸寸皲裂,该被世人指责,被蛇蚁啃噬。
“神父大人,我好害怕,那些梦好真实。如果有一天,我再也分不清梦境与现实,在白日中也情难自禁的对他做出了那些过分的事情该怎么办。”女子似乎的确很无措,嗓音中都带上了一丝哭腔,被背德的痛苦煎熬着内心。
教皇此时本应说一些劝解的话,可他的唇瓣微动,那些话却像是尽数堵在了喉咙之中。梦会侵蚀现实,女子的言语像是将他心中辗转反侧,思虑挣扎的心思摊开暴晒在了日光之下。
教皇扣紧了自己的掌心,他第一次希望正在告解的人不要再说下去。他想让她离开,他根本无法代替神来宽恕她的罪孽,那一字一句都像是刻印着他的罪孽。
教皇闭上了眼眸,“梦是假的,你不应该被无稽的梦所影响。仅是心中所想,而未做出实际行为,即便是神祇,也无法做出审判之举。”
“你的意思是,让我藏好心意,永远不要显露在人前对吗。”阮姝娅呢喃的说道,“是啊,我是如此的肮脏,心中充斥着污秽的欲念,这样的我根本就配不上他。”
迷途的羔羊诉说着自己的“污浊邪恶”,可她根本不知道,与其他的告解者相比,她所忏悔的事情是如此的可爱单纯。
教皇眸中泛起不忍,他身躯内的骨骼隐隐作痛。他无法再确定自己的公允,甚至怀疑他是在用自己的私心在拒绝她,规劝她,为她划定了一个格子将她禁锢在其中。
而她甚至并不知道正在倾听的人是他,她将他当做了一个可以信任的神父,只会懵懂的自责。
“你很好,不必看轻自己。”教皇想要安慰她。
女子摇了摇头,她的腰肢纤细,坐姿端正,礼仪得体,却像是一具破碎的美丽瓷器,“神父,我不敢想象,若是有一日他发现了我的那些过分的觊觎,我该如何自处。他一定会觉得很恶心,他一定会厌憎我、嫌恶我,我绝不能让他知道那些梦,对,绝对不可以。”
阮姝娅抬起手臂,温润的白玉镯在腕部落下,在教皇的方向,只能够隔着那一道窄窄的缝隙,猜测她是在抹着眼泪,“神父大人,这样的事情我只能够向神倾诉,若是被他知晓了,我一定会自愧而死的。”
阮姝娅的每一句话都像是化成一道戒鞭抽打在教皇的骨头上。他一生清白,高尚无私,从不做有愧之事,可唯独对她,就像是清醒的踏入刀山之中,一步错,步步错,每一步都仿若在刀尖上行走。
“也许,他并不介意……我的意思是,他并不想你痛苦,也不会看低你…”那些本不该说出的,几乎像是含着私欲的言语自墙壁后传来。
“不可以。”阮姝娅甚至是有些失态一般的站起了身,椅子向后蹭了一段距离,摩擦在地板上发出了一阵刺耳的声响,“我不能让他知道我是这样糟糕的人,我要一直做他心目中优雅矜持的女子,如此丑陋的一面我绝不会令他发现,否则我一定无颜再活下去的。”
女子的情绪忍不住得激动,片刻后她才匆匆向他道别,“神父大人,抱歉,神也许不会宽恕我了,对不起。”
女子离开了狭窄的告解室,室内残留的余香也缓缓消散。教皇维持着站起身,似乎要推开隔墙拉住她的姿势,额角泛起一阵疼痛。
她不愿令他知道那些越界的……“情意”。可樊鵺却已经知道了,圣女根本就不清楚,她诉说的对象一直是他,她想要掩藏的心意也早已经被他窥探。
教皇前半生循规蹈矩,以最严苛的教条约束自己,可以无愧于心,无愧于神。可在见到圣女之后,他却唯独一次次的愧对她。
他并不应该站在告解室倾听信徒忏悔,而是应该长跪在神像之前,向神忏悔他自己的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