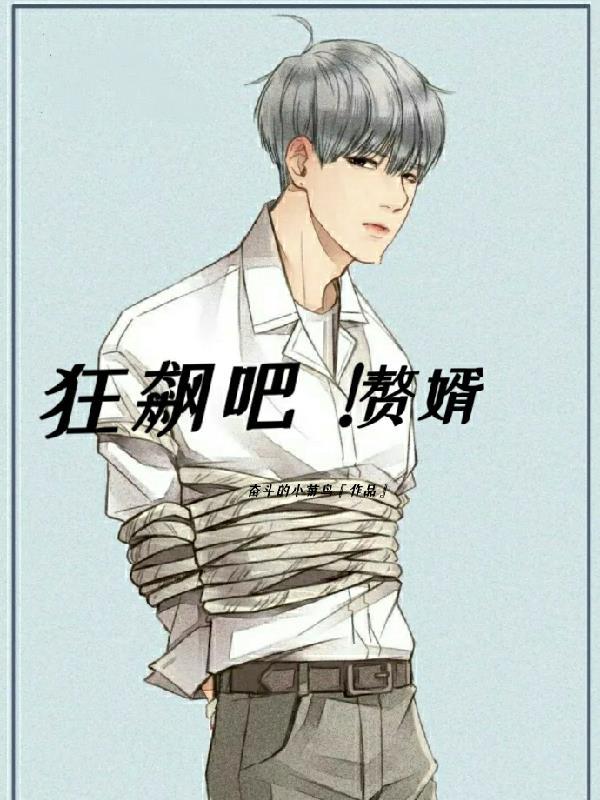UPU小说网>奈何明月照沟渠下两句搞笑 > 第60章(第2页)
第60章(第2页)
徐稚柳微微牵起嘴角,“其实不然,我约莫有个猜测,只是需要验证。”
那信里写了文定窑的情况,虽然户籍文书里没有详细记载文石之死和消失的数十万两银钱究竟去了何处,但处在这个关隘,收到这样一封信,徐稚柳很难不将文石之死和万寿瓷联想到一起去。
也只有万寿瓷,能撬动的了一个大窑户累积数代的家底。
然而,能通晓此间利害的,无非是和万寿瓷搭上关系的窑户。
整个景德镇除了湖田窑,也没几家。
吴寅看他心中有数,不再多费唇舌。两人因为此事紧要,又说了会话,吴寅干脆歇在书房,没有离去。
待到日上三竿,估摸再懒散的小孩也该起床了,他没让徐稚柳出面,随便点了名管事,就大摇大摆出了门。
不出半柱香,拎着个小孩回来。
不消徐稚柳如何盘问,那小孩看到一桌子的大鱼大肉,就禁不住诱惑说了实话。委托他的是个中年人,身子佝偻,驼背得严重,说话挺有条理,人也温和客气。
光这一奇貌,徐稚柳就想到了一人。
“果真是他。”
“谁?”
“安庆窑的账房先生名四六,我听叔父说过这人,他有过目不忘的本事,早年被王瑜从河边救回后就一直留在安庆窑,平日不好交际,鲜少出门,也就安庆窑还没壮大时,叔父在酒宴上见过几回,每每都是他出面帮王瑜代酒周旋,出谋划策。”
徐忠的原话是,若没有此人帮助王瑜打理窑务,经营盘算每一笔款项,安庆窑恐怕不会迅崛起。
他也不止一次动过挖墙脚的念头,可惜那四六是个水泼不进的家伙,平时见一面都难,更不用说挖到自家来。
“可是他和文定窑有什么关系?”
“文石的石,谐音作十。”
经得徐稚柳提醒,吴寅猛的反应过来,眼睛瞪得溜圆。
“那文石不是投河自尽了吗?”
转念一想,四六就是王瑜从河边救起的,难道那人就是文石?四六相加,不就是十吗?他和徐稚柳的目光撞上,在他微微点头示意后,不由惊叹!
“好一出置之死地而后生,那王瑜可知文石的真实身份?”
“应当不知,否则王瑜怎敢将账房交给他?”
再者,王瑜若当真知道那笔不翼而飞的数十万两银钱的去向,怀疑万寿瓷有碍,以他们双方如今对垒的局面,怎会刻意写信来提醒?
可如果换成是四六所为,就说得通了。
“我想他也许提醒过王瑜,但王瑜没有放在心上,他也不想表露自己真实的身份。无奈之下,就想借由湖田窑的手来阻止搭烧的进行,或是,让我起到戒备,一旦湖田窑有什么风吹草动,其他搭烧户们也会对此警觉。”
听到这里,吴寅只觉屁股着火,怎还和万寿瓷搭上了关系?要知道万庆皇帝爱瓷如命,又是逢十整数的万寿年,可不得大操大办吗?
这事儿早些年就开始筹备了,京中上下六部衙门并三司没有一个敢懈怠的。
别说出什么岔子,哪怕大朝会上稍微提一两嘴花费大,都要挨皇帝的板子。
他悄摸摸看过一圈,仍不放心,特地凑近徐稚柳,压低声音道:“你莫不是想错了?万寿瓷能有什么问题?难道还会吃你们的银子不成?”
“那你可有想过,为何事后,文石缄口不言?”
吴寅并非白身,什么事都不懂。那样的情况下,唯有交代实情才有出路,但凡能张嘴,文石怎会沉默?
“他必是受到了威胁!”
而以景德镇一方霸主的身份,又有谁能威胁得了他?
答案不言而喻。
是官员。
当时的县丞,是张文思。
张文思这个人,吴寅这些日子都看在了眼里,既是太监的走狗,又没几两脊骨,不敢得罪夏瑛,是以左右横跳,浑如一个跳梁小丑。
没有半点父母官该有的样子。
按照律法,他早就应该在婉娘事时就遭千刀万剐。可惜当时让他逃过了一劫,不想连十多年前的大案,他也牵涉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