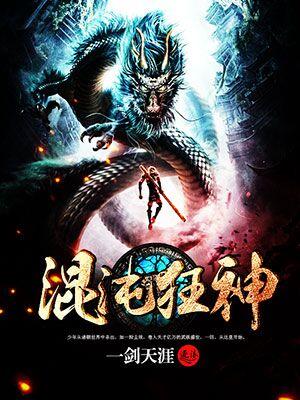UPU小说网>这个北宋有点怪 翔炎 > 第49頁(第2页)
第49頁(第2页)
弟弟丁兆蕙趴在木床上,露出半邊屁股。
丁兆蘭用燙過的小刀,割開臀肉,再把上面掛著的箭矢撥了出來,扔到一旁。
丁兆蕙發出一聲慘叫。
「幸好那丫頭力氣不大,用的是短弓,射中的又是腚部,箭矢只入肉三分。」丁兆蘭用驚魂未定的聲音說道:「要是被那白衣少年的長弓射中,我們兩人不死也得重傷。」
丁兆蘭一邊說著,一邊給弟弟的傷口處灑金創藥。
此時丁兆蕙感覺傷口沒有那麼痛了,他吸著氣說道:「那小女孩娃的箭也會拐彎,我聽風辨位,明明是躲開了的,但聲音又追了過來,然後就中箭了。」
丁兆蘭沉默著,他想起了之前的異像,然後說道:「弟弟,你有沒有覺得,我們被五鼠耍了。」
「他們怎麼會耍我們,要知道,我們都是松江人(舊上海),可是同鄉啊。」
宋人很講究同鄉之情,同村之誼。
「五鼠既然和展昭,也和那個白衣少年郎交過手,那麼必定也遇到過那看不見的牆,也肯定見識過會拐彎的箭。韓老二腿上那支箭,可和你臀上撥下來的那支一模一樣。」丁兆蘭哼了聲:「可他們可曾說過這兩件事?」
「沒,提都沒有提過。」丁兆蕙搖搖頭,他的表情開始漸漸變冷:「只說了展昭和那少年郎卑鄙無恥,偷襲他們。」
「所以說我們兄弟倆傻啊,人家說什麼就信什麼。」丁兆蘭嘆了口氣,滿臉鬱悶:「兩個打五個,就算是偷襲也是合情合理的吧?怎麼之前他們說什麼,我們就信什麼。」
丁兆蕙瞪大眼睛:「對喔,兩個打五個,就算偷襲了又如何!」
屋中氣氛沉靜下來。
兩個大男人臉上都是害臊之意。
特別是丁兆蕙,覺得丟臉之餘,他現在只想罵街。
這才興致勃勃地踏入江湖不到半個月,便被人耍了一頓,差點替人代死。
還虧之前他們認為自己兄弟兩人,很快就會闖下偌大的名聲。
現實便是狠狠一巴掌過來。
兩人沉默了好久,好一會丁兆蘭說道:「弟弟,你覺得那個少年郎的院子是怎麼一回事?」
「妖法!」丁兆蕙氣憤地說道,他現在鼻子還在隱隱作疼。
「就不能是道法,或者仙術嗎?」丁兆蘭反問道:「能在煌煌烈日下出現的術法,會是妖術嗎?」
丁兆蕙愣了下:「也對,有可能是道法仙術,輸給這樣的異人,我們兄弟倆似乎也不冤。」
丁兆蘭眼睛中滿是期待:「我想學。」
「那少年郎會教嗎?我們這才剛得罪了他。」
丁兆蘭搖頭說道:「我不知道,但我清楚,這世間,真正懂得術法的人,少之又少,我們如果錯過,一輩子再難遇到這樣的機緣了。」
「我也想學,可我清楚,那少年郎不會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