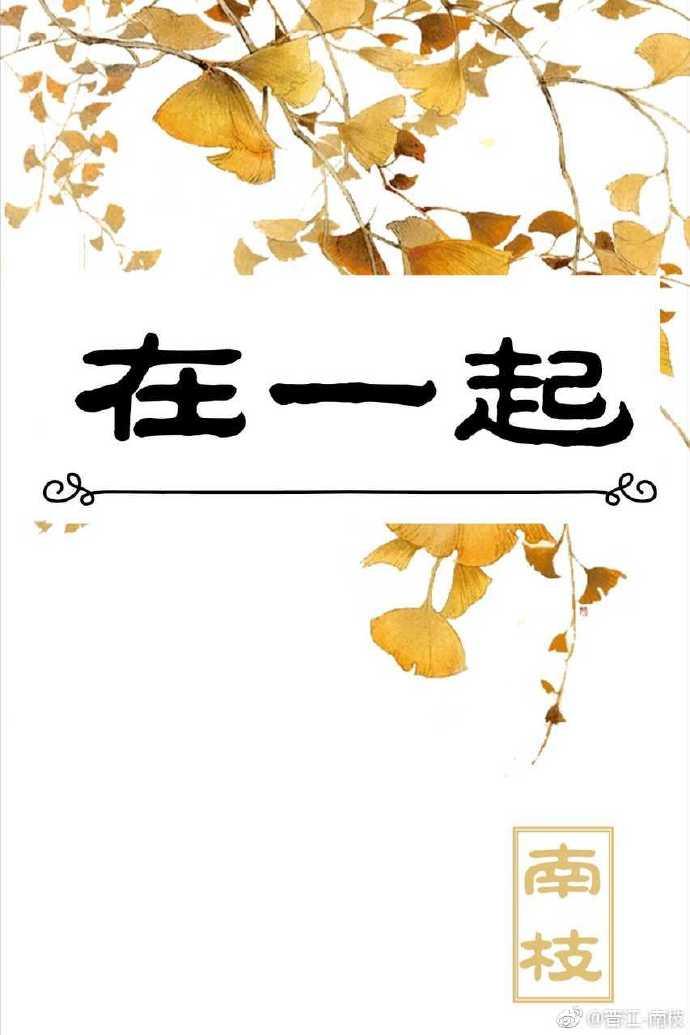UPU小说网>樱桃痣怎么预防 > 第91頁(第1页)
第91頁(第1页)
背景里有人討到好彩頭,又和同僚逗說樂子,付矜垣風幽默,和誰都對得上梗,好話百出,笑得眾人前仰後合。
玩開之後的歡樂場,沒有那端起來放不下去臭架子,讓人終於有了紙醉金迷的虛幻感,籌碼堆里令人驚嘆的小盒子和無數珍寶堆在一起已無人問津,闊氣的東道主又叫了三兩張桌子,反正地方夠大,時光悠閒,沒有窗子分不清晝與夜,什麼都不缺。
喝彩,謔笑,嬌嗔。
沒有人再注意這裡,他在溫柔地吻他,因為愛看他痛就讓他痛,愛看他哭就讓他一直紅著眼,他回答,「我這輩子從來就沒有後悔過任何事。」
「生氣了?」政遲哄著他,「是我做過火了。」
殷姚依舊垂著頭,五臟六腑扭曲在一起,重重揚起,又輕輕拋下,像淤血,破不開皮肉,沒那麼觸目驚心,但用力按下去也痛的。
大概是怎麼哄殷姚都沒什麼反應,政遲有些無奈,「消消氣。」
眼前遞來一把手槍,塞進他手心裡。
殷姚虛虛握著那把精巧漂亮的左輪手槍,動了動,不解地用眼神問他。
這手槍是付矜垣送給殷姚的,見面的時候開玩笑說給嫂子的見面禮,起初還覺得奇,但自從政遲把這玩具似的小東西玩到了殷姚身上,再看就覺的渾身彆扭了。
政遲不知怎麼,看見他和付矜垣說話就不高興。
殷姚一握著它就回想起冰涼的槍管和堅硬凸起的異物,覺得燙手,想扔掉卻被按住了。
「小心些,是填了彈的。」政遲垂下眼,握著殷姚的手,將那保險栓用拇指扶住,稍一用力,便扣了下來。
「……」殷姚不知道他想要幹什麼。
政遲耐心解釋道,「只有一枚,所以摸著份量差不多。」
只見那子彈從匣中滑出一個頭,又被塞了回去,指腹反扣彈巢,合上後蓋,再用力撥動,從外表看不出那子彈到底在什麼位置。
或許就是這一發也說不定。
殷姚好像明白他要幹什麼了,驚惶地掙扎,手卻被他用力握著,如何都抽不出來,「瘋了嗎!」
「你不是生氣嗎。」政遲握著殷姚的手,將那槍口對準自己的太陽穴,笑著說,「試試手氣?」
和殷姚的食指一起疊在扳機上,一用力就能將扳機扣下。
殷姚慌道,卻無法聲張,壓低聲音,「你別開玩笑,放開我!」
「不生氣了。」政遲湊近他,吻了吻額頭,湊在他耳邊低道,「別擔心,玩這個我運氣一直很好……」
「政遲——!!」
啪嗒。
殷姚的尖叫咽在嗓子裡,滿頭都是冷汗,大口地呼吸著,心跳似乎要撞破胸口,震到耳鳴。
政遲由上至下地看著他,將那溫熱的槍管放下,悶笑聲壓抑不住地變成大笑,在殷姚看瘋子一樣驚魂未定的目光中,心滿意足地將人抱在懷裡,「嚇成這樣?都說了,我運氣一向很好。」
這東西他玩多了,要是輸過,也不會還有命站著這兒。
說來有,當年被政成凌一怒之下發配出去,連張電話卡都沒留給他,渡過去之後身上連十美金都湊不到,能在地下和黑人用命拼出條財路來,是因為轉盤遊戲,他從來就沒輸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