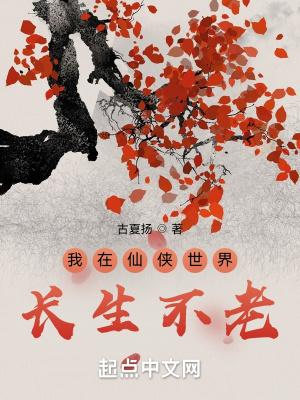UPU小说网>疯心难救免费阅读全文 > 第64页(第1页)
第64页(第1页)
余远洲走上前,冲着墓碑鞠了躬,出声叨咕了几句。无非什么季同现在很懂事,自己会照顾他之类的。叨咕完拍乔季同的后背:“走了。晚上咱哥俩好好喝一顿。”
“嗯。”乔季同跟着他往外走,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余远洲跟着他一起回头。
墓碑上刻着照片。年轻男女微笑着,在金色的夕阳下显得有几分温情。
这世间对死亡的恐惧,大抵都是对离别的恐惧。从生到死的列车一站站开,上车的人,下车的人。来的挡不住,走的留不下。
蓦地,乔季同哭了。手背擦着眼睛,委屈地像个走丢的小孩儿。
余远洲什么也没说,只是狠狠揉他的头,直到揉成鸟窝才罢休。
悲哀啊眼泪的,只能是一瞬。被死人抛弃的活人,还是得继续活。该怎么活,还怎么活。
他们肩并着肩,背着夕阳走在青灰色的石板路上,像两匹离群的小狼。
也许他们不会永远走在一条路上。但至少在当下,因为彼此的陪伴,并没有觉得太孤独。
作者有话说:
周四了周四了!今儿有双更!
第四十五章
俩人在附近的快捷酒店定了个标间,打算第二天中午再往d城开。
余远洲订了烧烤外卖,又在楼下小卖部拎了一打啤酒。回来的时候特意往停车场瞟了两眼,没看到大亮他们的车。
人呢?让往后稍稍,这咋还稍没影儿了?
他也没多想,以为大亮跟丢了。掏出手机了个定位,就回房去了。
兄弟俩许久没聚,今晚又不需要回哪里去。洗完澡穿着裤衩相对而坐,一边喝一边聊,就像十来岁时候那样。
余远洲酒量不行,半罐啤的下肚,脸颊就粉了。他拄着下巴颏儿,笑着问乔季同:“你还记得,你拿狗屎扔人那事儿吗。”
乔季同摇头:“不记得。”
“少来。你肯定记着。”余远洲又喝了一口酒,怀念地看着半空,“我高一那时候,班上有个傻B,到处宣扬我爸的事。还给我起外号叫「禽兽二代」,一天到晚追在屁股后头叫。有一回让你给碰上了,把你给气得呀。正好旁边有个流浪狗,蹲草坪里上厕所。你就蹲狗旁边瞪眼瞅着,狗也回头瞅你,一边拉一边哆嗦。我寻思你是想让狗咬人,在那儿等呢。哪想到那狗刚拉出来,你一把捡起狗屎,跑上来就抡那傻B后脖颈上了。那年你小学六年级。”
乔季同不承认:“你记错了。我没干过。那再虎也不能直接手抓啊。”
“对,再虎也不能直接手抓啊。”余远洲笑得前仰后合,“我带你回家洗手,一进门,我爷就从沙上站起来了。”余远洲从床上站起身,掐着腰使劲吸着闻味儿,“哎妈这啥味儿?哎妈。哎妈!”
学完又是笑得不行。
乔季同也乐,反击道:“你还说我啊?你自行车后座绑着个破海绵垫子,大红的,特别土。蹬得还贼快,从后面看像个红屁股的猴,在路上来回蹿。”
余远洲曲指对乔季同眉心一弹:“嘁!我那还不是怕你小子硌屁股!”
“下雨也不遮一下,都霉了。”
余远洲坐回床上盘起腿,脸上浮现出少年的得意倨傲:“我那垫子可是宝座,霉了小姑娘也都排队要坐。想当年,你哥在学校也算个什么草。”
乔季同小声怼他:“算婆婆丁(蒲公英)。”
“哎你小子!”
两人互相怼肩膀,笑着闹。笑着笑着,忽然屋里白光一闪,天边炸起了闷雷。
风往屋子里一灌,两人双双打了个寒战。
“有点冷啊。”余远洲起身去关窗户。这时又一道闪电晃下,就见酒店的院门驶进来一辆车。
黑色的越野大g,睁着对猫头鹰眼,从黑夜幽幽地滑进了光。车顶两个改装的大功率射灯,就像两道不熄的闪电。
乔季同也凑到窗边向外张望,感叹了句:“这车好酷。”
“季同,开房记的咱俩谁名?”
“我的名。”乔季同看向他,眉毛拧劲了,“怎么了?”
“···没什么。喝得有点多。”余远洲关上窗,拉上了窗帘,“十二点半了,困不困?早点休息吧。”
说罢又灭了主灯,只留一盏昏暗的床头灯。
乔季同担忧地追问:“余哥,哪里不舒服?”
余远洲站在窗前,没有说话。
又一道闪电劈下,映出他煞白的脸。额散乱,耷拉下来一绺在额角。镜片有点脏了,镜片后的眼睛也模糊不清。
乔季同上前揽住他的肩膀,安慰道:“春天的雷很快就会过去。”
余远洲点了下头。强装镇定地从床上捞起风衣,摸出烟弹盒,磕了一颗。
手抖个不停,怎么都插不进烟槽。
乔季同帮他插好烟,温热的手掌盖上他的肩头,轻轻摇晃。
余远洲急切地吸了一大口。可不但没冷静,反而抖得更厉害了。不仅是手,连肩膀都跟着抖。
乔季同抱住他,一边拍背一边安慰:“别怕。哥。别怕。我在呢。”
余远洲在乔季同怀里不停地吸烟,强迫自己冷静。
冷静。余远洲。季同还跟着,你不能慌。想对策,快想对策。
可这该死的大脑,一片空白。这不听话的身体,抖个不停。耳畔轰鸣,浑身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