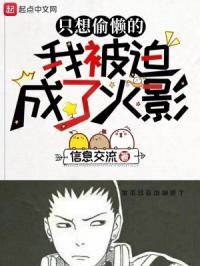UPU小说网>开饭吧小辉煌讲了什么 > 第88页(第1页)
第88页(第1页)
像是被抽去筋的鱼一样,他的背部贴在墙壁曲起,痛苦地抽搐,“我没有撒谎。”
他松开他,让他缓缓地沿壁滑下,蜷在墙角,痛苦地呼吸着。脸上已经青紫一片,嘴角有几道血痕,在白皙的肤色托衬下更是触目惊心。
“arron,看看你的样子?”louis蹲了下来,声音非常温和,和他脸上的狠戾表情完全不似“看看我们可爱的小天使。”他的手指划过他的耳背,脖颈,锁骨,暧昧地轻触着。“你母亲看到你这样,一定很心疼。”
他浑身都疼痛着,一个多小时的虐打让他对疼痛已经麻痹了,对方这种嘲讽的语言,他根本不放在心上。
他不怕疼,他也不怕继续被打。
他怕死,他怕自己再也看不到她。
辉煌,小辉煌。
脸上汗水和血水交织在一起,湿热一片,他把脸贴在冰冷的地上,试图找回一点可以让他清醒的记忆。
“你在想那个女人是吗?”louis的声音忽远忽近,“老实说,你当时的表情真的让我很回味。”
当时?
对了,是当时。
在他们的家里。
黑色的枪口指着她的脑袋,而她尚在昏迷。
你可以选择,永远不见她,让她好好活着。或是,像你母亲一样,你可以在医院一直陪她到死为止。
他没有选择。
无处可逃,退无可退!
他单纯地以为只要放弃他们觊觎的东西,远走高飞就能避其一世,安居乐业。
可面前的这个是疯子,这疯子最大的乐趣就是一手扼杀能让他感觉到快乐的一切事物。这样的恶意是直接的,犀利无法回避的。
他从来就不该侥幸!
“我在想,那个女人看到你留下的信会是什么表情?”脚尖勾起他的下巴,灰色的眼眸对上他的,“说真的,你的眼光让我很失望。”
他半眯着眼睛仰着头看着这个名义上的二哥,笑容诡异,“louis,她的拳头够硬吧!”。
louis的脸还青着一块,颇有点狼狈。
他的小辉煌,真不愧是女王殿级,比他有勇气多了。
不待他多得意一点,皮鞋已经踹在他的腹部,把他踹得蜷起,“你和以前一样,总是躲在别人身后。装成弱者的样子搏取同情。”
他的脸贴在微湿的地面,耳边传来细碎的石头刮蹭的声音,“你母亲和你是一路货色,你们就像是寄生虫一样地活着。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谁提供的护庇更强大你们就躲在谁的身后。”他的嘴抿着一条直线,“我不得不说,你的眼光比你母亲差得多,差得太多了!”
每一下的呼吸都牵引着肺部的疼痛,他短促地急喘着,一点一点地抚平呼吸。心里却想着,你懂什么,被自己爱的女人爱着,护着短,这样的幸福你会懂?
他闭起眼,不听他的话,不回答,一心想着那张鼓嘟嘟的脸,回味着那痛快至极的一拳。这样,身体根本就感觉不到疼痛了。
下一刻,他栗色的头发被粗暴地揪起,下巴和胸骨绷成一条线。灰色的眼眸直直刺入他的,“那个女人那里吸引你?”他用力掐住他的左手,“要不是得留着你的右手签字,我倒不介意一齐折了。”
剧烈的疼痛让他不停地倒吸着冷气,冷汗涔涔。可是却满心安慰,毕竟她安全了。louis下手是出了名的狠,麻醉针后还不忘要加一记手刀,她纤细的脖子怎么受得起?好在自己基本防身术也不是白学的,但即使如此也抵不上对方自小受训的身手。
“arron,为她赔上一只手值得吗?”他阴亵的眼神像一条冰冷的毒蛇。
他黑亮晶莹的眼睛甚至是带着得意地看那个暴戾的男人,骄傲满满,“你会懂吗?”
对方的手狠狠地扼住他的脖子,恶狠狠地,“我不懂,我当然不懂。我永远也不想知道你这强盗在想什么!”
喉部一阵压迫,空气越来越稀薄,他眼睛热热的,似乎有什么要流出来。蓦地,对方松开手,他直直摔在地上,双耳轰鸣,眼前一片模糊,声音远远近近地传来,
“wrence……找到他了,……不,你不必来,明天我就带他回去。我想他会很高兴见到你。”
身体放松后,剧烈的疼痛开始席卷全身的神经,胸口闷堵得不能呼吸,口腔和鼻腔每呼入一口空气就似火烧灼一般,辣辣地疼痛,像是一把刀在上下刮蹭着。
少顷,头被托起,冰冰的液体灌进口中。这对于火辣辣的喉咙不啻是种刺激,灌了几口,他被狠狠地呛到,剧烈地咳嗽起来,喷出的液体混着血丝。
“我差点忘了,我们的小天使有旧伤的。”比冰水更冰冷的是声音,浓烈的酒香混合着灼热的气息喷在他耳边,密密麻麻,“arron……欢迎你回来……”
—————————————偶是资本家刚风尘仆仆回家的分割线————————————
谭清从计程车上拖着行李下来,长时间的飞机搭乘让他在踏上陆地时,有种习惯性地晕眩,身子有点不由自主的摇晃。他现在只想回家洗个澡,好好睡一觉。
一个灰扑扑的人影蹲在警卫室外的花圃边上,侧着脑袋,半露出来的脸面色晦黯,眼睛肿得和桃子一样,一身颓废却杀气腾腾。
谭清松松领带,感觉口水吞咽都有点困难。他这是怎么了?一个路边乞丐也让他有点心惊?他皱着眉头却还是小心翼翼地在经过那个人的时候,明显绕开一圈。
豪华住宅配的门卫很尽职且记忆力好,啪地行了个李,“谭先生,您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