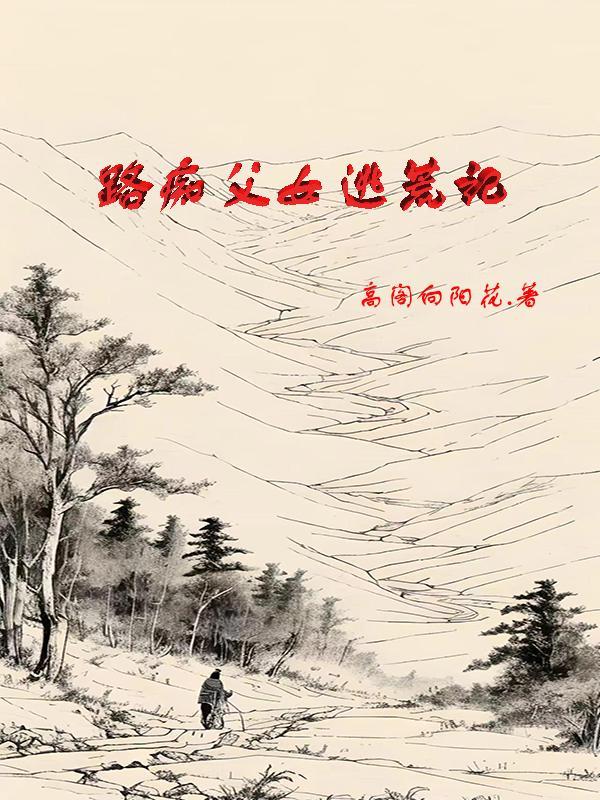UPU小说网>剑侠情缘剧 > 四十七 穿心(第1页)
四十七 穿心(第1页)
章敛摇头道:“哎对了,我忘记问他们了,你们最近都不过来这边,这些病人和女眷的饭食之类是如何供应?患者必须要保持至少一定量的进食、饮水,方才有可能恢复康健,你们若将他们就这样弃之不顾、自生自灭,我就算是华佗在世也药石罔救。”
三当家笑道:“内务就是区区不才在管。你刚才也看了,后山本就有伙房的,附近村里的农夫经常过来,送食材上岛,我也没让他少了后山的份。以前是后山伙房供应全寨子的吃食,现在被隔离了,就只供后山了。那厨子没病,却被关在后山做饭,原还天天在这哭求,这两三日许是认了命了,没见他再出来闹了。欸,他刚才没找你说道啊?”
章敛笑道:“我教给了他些能加强体魄、预防疫病的法门,但愿他在后山能不染上病,多做几天饭。”
三当家跟着笑:“对对,还是章大夫想得周到。他要是死了,我还得新抓厨子去后山,麻烦不说,像他体格这么好、这么扛造、不容易染上病的,那可真不多了。”
鹿鸣涧:“……”
这三当家的,之前还道他是个读书人进了贼巢,兴许是被迫的,没想到蛇鼠一窝,想法和其他贼匪一样草菅民命!
三当家咂摸了一下嘴巴,回头道:“章大夫,啥法子啊,也教教我呗?”
章敛摆手道:“五禽戏之类,给没有根基的百姓用的。三当家你天天跟着寨中兄弟操练,早用不上这些粗浅的法子了。”
三当家这才作罢。
————————
师徒二人随着三当家回到寨子主殿,见那庞虎文手握长枪,正在演练。出手激烈而迅捷,犹裂石穿云。
三当家就鼓掌大声喝彩道:“好一招暴雨梨花枪!不愧是将军的成名技!”
庞虎文利落收枪,将武器背手立于身后,回过身来,睥睨着走近来的三人,离了有数尺时便用手势示意他们停步,仍保持着阴鸷神情道:“如何?”
三当家躬身退开几步,让出章敛。
章敛拱手抱歉道:“章某才疏学浅,不能尽识此病,只得先以药物压制病情。待章某回去遍查医书,望能有所现。五日之后,章某再来登门,看病人情形如何,庞寨主还请稍安勿躁。”
庞虎文仍是那副阴鸷神情,但没有为难章敛,唯哼了一声道:“五日,就五日。但愿章大夫能给本将军带来好消息。”
鹿鸣涧心底对此人态度十分恼怒,却未动声色,知道此时以赶紧离去为第一要务。
此时,一水贼匆忙跑进了大殿,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口中疾呼:“将军!三当家!大事不好!走水了!多处走水了!”
章敛暗自皱眉,口上却平和道:“既然寨主有事要处理,那章某就先告辞了。”
说罢,便拂袖转身,招呼了鹿鸣涧跟上。
鹿鸣涧亦微觉不妙,真气运转而不显,贴紧了章敛几步,又刻意克制,未现出慌乱逃离之态。
还未走出殿,便又有数贼来到殿中,皆是赶来给庞虎文报信,各说各的,吵闹不停——
鹿鸣涧耳力过人,虽听不真切连贯,却捕捉到了“人都不见”之类的话语,霎时脚下加快,御风而起,手上亦凝起薄薄混元之气,欲护着章敛紧急撤离。
几息之后,庞虎文勃然大怒道:“贼子休走!”
一柄长刀被他从身旁武器架上铮然抽出,照着章敛背心便直直掷来,破风穿云,其势竟疾如弩箭!
“师父你先走!”
鹿鸣涧汗毛直立,一边挡往章敛正身后,一边转身戒备,混元真气从指尖暴烈而出,将这已迫在咫尺的长刀击落!
刀柄先掉在地上出巨响,继而刀身倒下,锋利的刀刃楔进木质地板,露于外面的半截犹流动着凶光。
鹿鸣涧出了一身冷汗。
倘若她出手再慢半刻,就算有负在背上的药箱可帮忙缓冲一下力道,但以此刀之锋、庞虎文之劲,怕不是刀身亦可穿过药箱,将她透胸而过!
可她还来不及后怕,一道金红身影便疾风一般掠过了她身侧,抢至她身后!
鹿鸣涧心下一沉,随之再次转身,便见到银亮枪尖舞作一团朝自己戳来,如染血梨花锦簇繁盛,白红乱舞,欲迷人眼。
她没来由地想到了刚才三当家说的,这庞虎文的成名技“暴雨梨花枪”,却原来真能快似花团!
对方枪势如电,鹿鸣涧无法力敌,只能先退避,待以“瑶台枕鹤”撤开几步,她重新站定,看清了眼前状况,心脏倏然停跳——
章敛匍匐在庞虎文身后,一动不动,青丝委地。
————————
鹿鸣涧若遭雷击、心胆俱裂,怔忪之下差点没避开庞虎文再次攻来的长枪——
她此时方如梦初醒,庞虎文枪尖那鲜血,不是章敛的又是谁的!
庞虎文阴沉愤怒地问道:“你们好谋划……好大的胆子,算计到我头上来了!说,同伙是什么人!藏在何处!”
鹿鸣涧不答,庞虎文气极反笑,仗枪再次袭来。狼狈不堪踉跄着,鹿鸣涧翻滚了几番,却始终逃不出庞虎文的枪风范围。
当庞虎文将鹿鸣涧逼入墙角,以为她避无可避时,他狞笑着欺身而上,她却以一个怪异的姿势翻折,以“太阴指”袭上了庞虎文小腿要穴,暂时拖缓了他的行动,自己拧身而走,跳将起来朝着师父奔去——
章敛就趴在离殿门不远的地方。
三个报信的水贼在旁观战,因为知道庞虎文生有怪癖,喜欢以残酷手段折磨人来取悦自己,故而没敢出手相帮。此刻,见庞虎文未能片刻之间尽杀二人,一人急道:“将军,快些了结,火势要烧到大殿来了!”
见庞虎文不闻不答,双目赤红去追那万花少女,三人互相看一眼,皆争相恐后奔向主殿大门,各自不知是救火还是逃命去也。
鹿鸣涧奔到近前,见章敛脸朝地面,被从后方一枪贯心。披着的黑袍浸了暗红而不显,只是颜色更深些,一滩深红从身下漫延开来。
她不敢相信,不敢相信这么多年、死里逃生这么多次的师父,就这么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