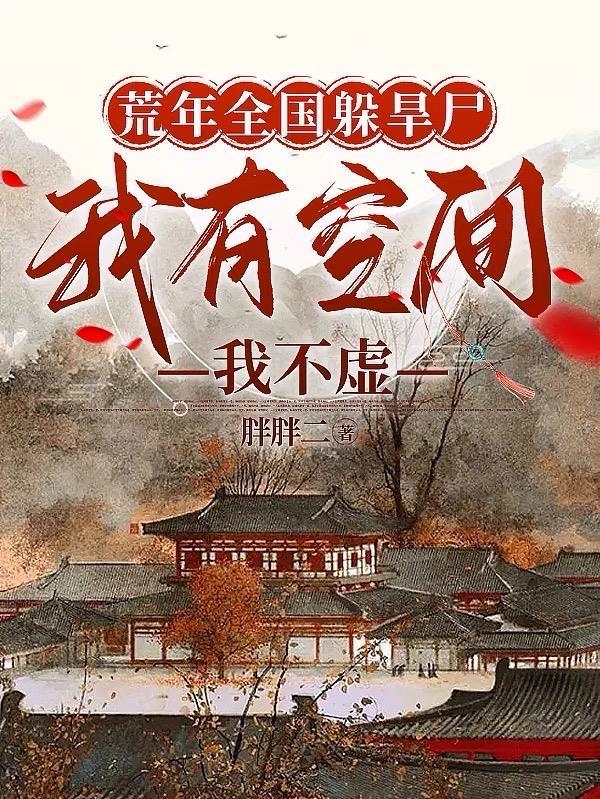UPU小说网>纾春指的是什么 > 第38章 狗与狗不同(第2页)
第38章 狗与狗不同(第2页)
拾叶低下头,跪在上:“教习说,此次是奴难得之机,定要好好做。”
“还有呢?”
“教习还说:她喜好特殊,奴该有的手段要有,假若她。。。。。。她要用强,就让奴从了。”
郭久给了拾叶一个警告的眼神。
韦大人最烦这种男男女女的龌龊事了,怎么还口无遮拦把话说这么透彻?
再偷偷看向韦不琛,见他正怒视着自己,连忙解释:
“教习也只是想要拾叶尽快得到崔小娘子的信任。毕竟她有些与众不同。”
韦不琛背过身,手撑在书案上,深吸了一口气:“出去。”
他深知教习所言没有错。
线人,为求信任,无所不用其极,男女之事都是手段。
更何况她那样的人,根本不会在意这种男女大防,身边有个俊俏的护卫,她定然是乐在其中的。
可他还是忍不住怒了。
她这一头给拾叶绣着小狗,那一头又跟6铮做些见不得人的事!
究竟有没有一点妇道?
他不由想起太虚武馆的那个昏,她站在夕阳下,鹅的衣裙衬得她那样娇俏可人。
谁能想到如此纯真的皮囊下,竟藏着一个不安分的灵魂?
分不清自己心里那几丝烦闷是什么,直觉告诉他不要去分辨。
手握成拳,又放开:“郭久。”
郭久从门外进来,听候差遣。
韦不琛转过身,神色已恢复平静,冷声下了命令:“去帮拾叶找到推她入河的人,助他尽快进入内院。”
“是。”郭久又问,“银台司的请令,必是圣人授意,大人预备如何应对?”
那日在茶馆,紫衣姑娘说得很明白,擢升的旨意都拟好了,却始终没有下。这时候银台司来请令,其深意不言而喻。
“照实说。”韦不琛又开始奋疾书。比起拾叶衣裳上贴的碎布头,他身上绛衣穿得太久了些,彘兽绣纹洗得有些白,甚至彘尾还绽开了线。
郭久跟随韦不琛已有多年,知道他心中有傲骨,但当了绣使,这傲骨就该剔干净了,越留就会越煎熬。
就像拾叶做线人,教习就会说,该上的手段就要上,该舍的就要舍。
“大人,有些话,属下本不该说。但您——”
“那就不要说。”韦不琛打断他,抬起头道,“蔡胜远等人,追查得如何了?”
蔡胜远是绣使一直在追查的几个叛军,之前在京城出现过,绣使布下罗网,哪知被崔礼礼横插一杠子搅了。
“我们一直在跟,现在有线人说往定县方向去了。”
定县在北方。如今邯枝国的动静不小,他们往那头去,目的绝不简单。
韦不琛放下,将写满字的纸折好,放入信封,又滴上蜡油封缄。
“务必将此信三日内送到宁永县罗氏绸缎庄。另外,你派几个人去定县,看见人了,不要打草惊蛇,蔡胜远若要北上,跟着就是,但决不许离开芮国边城。每日一报,不得有误。”
“是!”大人这是要大作为了,郭久见韦不琛站了起来,“属下去备马。”
“去银台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