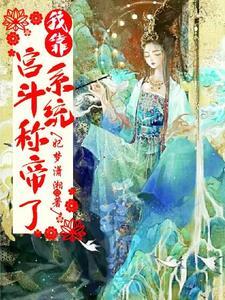UPU小说网>女扮男装权臣古言 > 第288章 传证人(第1页)
第288章 传证人(第1页)
慈宁宫内,熏香寥寥升起,安静而又祥和。
太后握着一串佛珠,低声诵着经文。
自皇上登基后,太后的心便淡泊了许多,每年冬日都会去寺庙常住,新年回来后,清明之际,亦会去礼佛。
无人知道太后此举为何,但跟在太后身边多年的婢女知晓。
等太后的经文颂完。
她才道:“太后娘娘,牢里送了一封信来,说是许姑娘让其转交的。”
太后并未接信,而是问道:“刚刚听见鼓声,谁在外面击鼓?”
“听说是二十多年前大理寺卿的家公子,邱瀛。”
二十多年前,邱家。
这个名字,太后也并不陌生。
看来,许愿是铁了心的要在今日大闹上一场了。
太后又问道:“还有谁?”
“很多人。”侍女如实道。
许家当年门生众多,许家落难后,那些门生为其奔走,亦是死的死,伤的伤,被贬的被贬。
如今伸冤,不只是为了许家,更是为了他们自己。
“看来,那份名册,在许愿手里。”
太后说完,唇角间浮现起来一抹笑意,她喃喃道:“你教了一个好女儿啊。”
侍女不知如何接这一句话。
遂低下头,沉默不语。
“何人接的案子?”
“大理寺卿,孙文杰,而后皇上又命常御史负责此案。”
太后眯了眯眼,有些不敢相信:“还能惊动常御史?”
侍女道:“歌舒可汗来访。”
样子总是要做得。
太后了然,不再问话。
侍女又问:“太后,不看这一封信吗?”
“无非就是劝哀家看在许家的面子上,还许家一个公道,不看也罢。”
太后伸出手,侍女扶了上去,问道:“太后娘娘,去何处?”
“睡一会儿,你替哀家去告诉常御史,不论今日结果如何,务必留许愿一条性命。”
侍女颔道:“是。”
她刚刚离开,另外一个侍女慢慢进来,见到太后时,跪下道:“太后,三皇子求见。”
“不见。”
“三皇子说,太后若是不见,还请看看手中的信,在做决定。”
——
承恩殿
文武百官两侧而立,皇上坐在最前面,而后便是歌舒鞑。
比起歌舒鞑笑容满面,皇上的脸上并不好看。
甚至于是难看。
不过他是帝王,喜怒不形于色。
因而在旁人眼里,全是威严。
歌舒鞑先开口道:“天齐的皇帝,并非是吾一定要插手你们天齐的政事,只是当年许家因歌舒而落难,被传通敌,天齐多少百姓谩骂歌舒,歌舒还因此与天齐交恶二十年,今日吾在此,也是为死去的大可汗寻求公道。”
歌舒鞑说完,迟迟没有人接话。
北尧见此,开口道:“大可汗言之有理,而今的天齐崇尚和平,四海之内,皆是兄弟,自会查明真相。”
“是啊,歌舒兄无需担心。”
皇上也跟着开口。
与此同时,大殿之外,有人高声喊道:“带许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