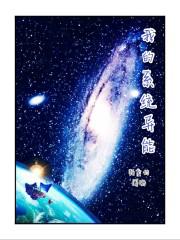UPU小说网>冬绥夏安是什么意思 > 第77頁(第2页)
第77頁(第2页)
夏安一把拉住他,可憐兮兮地沖他眨了眨眼:「等等我。」
可惜冬綏從來不吃糖衣炮彈這一套。他義正言辭地掰開夏安扒著他的手,態度堅決:「不行,你作業還沒寫完。」
於是夏安長吁短嘆地捧起作業,裝模作樣地念著詩:「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冬綏毫不留情地戳穿他:「你拿的是英語作業。」
夏安:「咳咳,hoareyou。。。。。。」
一口流利的中式英語,冬綏無奈扶額,他實在是不知道該怎麼評價夏安那蹩腳的英語水平。
「不學了!」夏安猛地把作業往桌上一拍,豪氣干雲地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詞:「古語有云,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我苦作業已久,久困樊籠,如今,不反也得反了!」
冬綏實在沒忍住,翻了個白眼。
白眼還沒翻完,就被人一撲,一把撲到床上。
天旋地轉間,夏安那張明艷而又極具衝擊力的臉不斷逼近,近在咫尺。
「好啊冬小綏,你敢翻我白眼了。」
冬綏試著掙扎了一下,無果,便放棄了,由他怎麼來。
但是看著那張令人怦然心動的臉,還有迫近的清淺呼吸,他還是忍不住紅了臉,心跳得好快,幾乎要破開擋在前面的那層淺薄的皮肉,跳出胸膛。
「你先放開。」冬綏蹬了蹬腿,還是毫無效果,就只能拿眼睛瞪他。
但這無疑使夏安更興奮,他更深地鉗住冬綏的雙腕,撐在他身上。
這個姿勢。。。。。。真的很難不讓人想歪。
冬綏羞憤地別過臉,儘量避免與夏安的視線相交。
「冬小綏居然敢造反了。」夏安不懷好意地笑了笑,一雙手不安分地在冬綏身上游移著,準備使出那一記殺招。
終極奧義——撓痒痒!
夏安立刻撓遍冬綏身上的痒痒肉,撓得人滿床打滾地躲著他,痛苦的笑聲不絕於耳,間雜著微弱的求饒聲。
為什麼說微弱,實在是因為,冬綏笑得沒力氣了。
到最後,冬綏實在是連抬手的力氣都沒了,只能任由夏安擺動。
夏安也跟他並排躺在床上,看著空洞的天花板,休息了一會兒,又精神了起來,興致勃勃地開始煩冬綏。
「小時候我媽就喜歡撓我痒痒。」夏安說。
冬綏動了動手指,勾了勾他。
「因為我總不聽話。我媽捨不得打我,就撓我癢。」夏安說著,忍不住笑了起來。他偏頭看冬綏,狹長的流轉眼眸中閃爍著一些晦暗不明的情緒。
「阿姨厲害。」冬綏實誠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