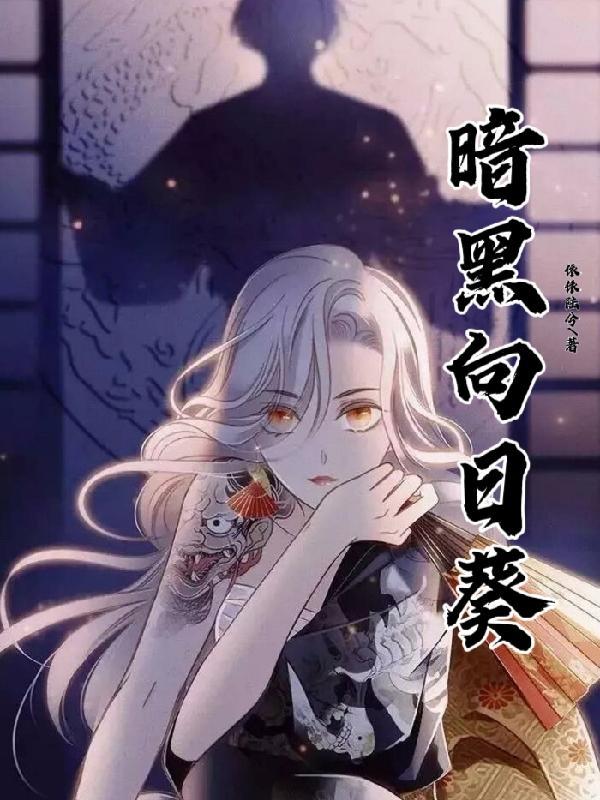UPU小说网>三生缘歌曲 > 第32章(第2页)
第32章(第2页)
那蛇并没追出来,应该受了重伤。在云冰祁的揽护下跑了很久,直到钻进一片竹林里江浸月才想起他好像挨了一鞭子的事,遂问:“你没事吧?”
“没事。”话音刚落,他整个身体便直直向后倒去。
“喂!”江浸月吓得不轻,但见他脸色苍白,嘴唇已变得青紫。
中……中毒了!
扶起云冰祁来往背后一瞅,顿时大骇——汩汩鲜血如朱砂渐染,顷刻间就染红了他的白衣。正要解开他衣袍检查伤势,颤抖的手立马被怀中人握住:“别碰,有毒。”
江浸月的心仿佛被谁狠狠拧了一把,有种莫名的情绪自心底袅绕而起:“你……你怎么样?别吓我。”
“放心,没事。”
在这陌生的梦境里没有雪纤,也没有办法为他解毒,她该怎么办?看着云冰祁安静枕在自己肩上,江浸月慌了手脚,患得患失的心理总是这样令人害怕。第二次了吧,她记得他中摄魂蛊那天,也是这般无力地躺在自己怀里。
这样耗下去不是办法,江浸月
扶云冰祁靠上一棵粗竹,自己则与他相对盘腿而坐,以妖灵逼出内丹将他体内之毒转移,这是她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即便她那丁点修为远远净化不了毒素——可至少她能挨到走出梦境那一刻,这比带具尸体出去划算多了。
也不知捣鼓了多久,等那颗蓝光清溢的内丹被暗紫色毒素包围时,她觉得再也自己撑不下去了,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伟大地舍己为人,可是丫的好像足以搭上性命了啊!
毒素扩散,寒气流窜,她仿佛瞬间被扔进冰窖般,哆哆嗦嗦喊一声冷便晕了过去,迷迷糊糊看见一双清明的凤目,然后跌进一个温暖怀抱。
雨似乎还没完没了的下着,云冰祁抱着江浸月躲入徇山中一座破旧雨亭,摇摇欲坠的模样好像风一吹便会坍塌。怀中人又瑟瑟地钻了钻,冰凉的手穿过衣袍贴上他温热皮肤,死死抱着。背上的伤口还隐隐作痛,云冰祁眉头紧锁,仍旧没有明白中毒的怎么变成江浸月了,莫非她替自己吸走了毒?
“好……好冷……”她抖着嘴唇低声哼哼,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云冰祁索性脱下外袍来将她裹了个严实,心中是说不出的滋味,怅惘或者温暖,宛若春日里兜头淋了一场杏花雨。抱她的手不由紧了紧,这样会不会好一点……
可是看着她面色红润、呼吸匀称,与自己相比截然不同,哪有一点中毒的样子?
江浸月觉得
这蛇毒对自己的影响似乎并不大,除去着实冷了些,脑袋晕了些,思维却还明朗着。她记得追着花淅出去那晚遇上这家伙自己便晕了过去,醒来是被秦更阑捆在山洞里,虽说没有光亮,可她还是能隐隐看见方才那个洞和秦更阑所在的那个甚为相似。莫非……那条赤练蛇便是秦更阑,双生花的生存原理并不是说颠覆便能颠覆,除非换个原身,那么看样子她是在洞内闭关修炼,不小心叫他们误闯了进去。
一定是这样!江浸月刚想睁眼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云冰祁,耳边就响起一声炸雷,脑子顿时轰鸣一片,熟悉的撕裂感再度袭来。
“啊……”她不由低呼,紧紧环住云冰祁的腰,任他将她护进怀里。脑袋疼得几欲炸开,带着她的意识也模糊起来,只觉那淡雅幽香渐渐飘远,睁开眼身边的人早已不在,仿佛至始至终都是她一个人一般,世界混沌一片。
风声、雨声、雷声疯拥入耳,江浸月又听见花淅惊慌地喊了一声:“哥哥!”睁眼间,竟回到了那阴冷潮湿的山洞。
山洞里烛火摇曳,待看清眼前这一幕时,她觉得她整个人犹若再次被扔进了万道惊雷里:花怿赤裸着上身闭目坐在石床上,一如超脱美色的僧人,又如失去斗志任人宰割的鱼肉,而秦更阑也穿得格外凉快像一条蛇般缠在他身上,她一只纤长玉手勾着花怿的脖子,另一只则不
停抚摸他的脸庞。
花淅双眼噙着泪,身子前倾似乎快挣断捆她的铁索。“哥哥,我求你,不要这样对我!”几近崩溃的哭喊。
秦更阑看着视若无睹的花怿,妩媚的笑冷却几分:“一点诚意都没有。”
“你想怎样?”花怿面无表情。
“亲我。”
江浸月顿时觉得自己又被扔进了无垠地火。花怿紧闭的双眼倏然睁开,身体依旧一动不动,还好没有欲火焚身。耳边又传来花淅的哭喊:“疯女人!你放开我哥哥!你个贱女人,不要脸!”
江浸月便突然明白了花怿为何任秦更阑揉躏,感情他是拿自己来交换他妹妹的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