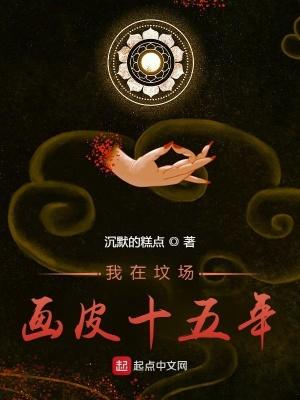UPU小说网>罗曼史的 > 第53章(第1页)
第53章(第1页)
陆远山眼中笑意更浓,“那你的意思是以后你就看看,我也不必买了。”
岳青宝连忙摇头,夹了一颗圆滚滚亮晶晶的白玉丸子放到陆远山碗里,“你平时劳苦功高,每天奔波,自然要吃得好一些。”
这段时间朝夕相对,岳青宝是个惯会见风使舵,以柔克刚的人,从前对岳秉国是这样,如今对陆远山仍旧是一样的计策。岳青宝知道他吃软不吃硬,便笑眯眯地同他说好话。
陆远山从来就知道这个瓷娃娃生得漂亮,可是漂亮的人他见得多了,可是谁在他眼里都不如岳青宝一样有趣生动。
岳青宝被他的眼神一望,轻咳一声,不自在地转开了视线。
夜里转醒的时候,岳青宝习惯性地去摸床头矮柜上的水杯来喝,她咕噜咕噜地喝了两口水,才转头去看熟睡的陆远山。
他一向警觉,稍有动静,就会醒来,因此,岳青宝的动作很轻很慢,她放回水杯,小心翼翼地拉开矮柜的抽屉,从里面取出一个木盒,在里面放着的丝绒垫下摸出一颗白色的药丸,就着白水吞了下去。
这种西药不宜久吃,岳青宝担忧地想,不如还是去抓些温和的中药,可是她若是吃中药,陆远山一定会察觉,不过,她也不知道陆远山究竟是怎么想的。
她到底是他的什么人呢?
岳青宝吃过药又躺回枕头,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过了几天,正值周末,家里来了两个意外登门的客人,正是苏亚与朱郁夫。
岳青宝独自在家,正觉无聊,便高兴地把二人请进门来。
苏亚见到齐整的小院花草,赞道:“青宝小姐的花园像是用了许多心思,打理得这样井井有条。”
岳青宝笑了起来,“我不过尔尔,从前家中有一个得力的花匠才是厉害,偌大的庭院花朵争艳,夏日里还有一泓瀑布似的花帘,灼灼开放,煞是好看……”她说到后来,心中不免又有些难过,只得笑了笑,不再说了。
苏亚并未察觉,“原来如此,那是师出有门了……”
岳青宝请二人到了客厅,动手泡了一壶香片。
朱郁夫见屋中归置整洁,窗明几净,沙发前的茶几上随意摆着几本书册,便道:“青宝小姐虽然独居,可也是自得其乐了。”
岳青宝赧颜一笑,想要解释一番却发现又无从说起,只得说:“家中还有一个徐妈妈负责看顾饮食,帮了许多忙。”
朱郁夫点点头,转而问起岳青宝的工作近况。青宝便一五一十地说起跟随孙译成做通译的工作。
苏亚听得有些佩服,“我家与孙家有些交情,听说孙译成年少有为,你能跟他学做生意,大有裨益。”他停了片刻,试探地问,“不知你是如何寻得这样好的职务?”
岳青宝答道:“从前见过,又有人引荐。”
苏亚沉吟片刻,近日里听说陆远山养了个外室,他心中有些怀疑,便来探岳青宝,可见她眉目如旧,住处也未见蹊跷,一时也不知道这外室究竟到底是不是岳青宝,陆远山在城中赫赫有名,可是身旁的女人几乎绝迹,苏亚之前见过二人交往之状,也不知道二人究竟是何关系。
苏亚抬头仔细地看了一眼岳青宝,心跳快了一分,他从第一次相见就喜欢这个眉清目秀,举止大方的岳青宝。他端起茶杯,呷了口茶,仿佛漫不经心地问:“你是否与陆远山有些交情?”
岳青宝不明所以,只得点头。
苏亚又道:“近来城中有件趣事,说来与你听听也无妨。听闻陆远山养了个外室,不知你可有听说?”
外室?是在说我吗?岳青宝乍一听见,只能茫然地摇头。
苏亚见她脸上并无变化,似乎也不大在意,便有些高兴。
三人又聊了一会儿旁的事情,徐妈便回来了。
徐妈见到屋中两位年轻的男士,有点心惊肉跳,这个岳姑娘胆子太大了。她出声问道:“姑娘,晚饭想吃些什么?”
听岳青宝报了几个菜名儿,却没有留客的意思,苏亚和朱郁夫便告辞了。
岳青宝慢半拍地想起“外室”二字,才渐渐回过味来,越想越生气,饭没吃完,就回房气呼呼地躺在床上。
过去周姨娘和蒋姨娘在家中地位,她也见过,从前余三那么大阵势娶她当太太,她都不愿意,怎么到这会儿子,居然就成了一个不明不白的外室,连姨娘都不如。
岳青宝心中不痛快,简直想一走了之,可是一想到,在北平有宅子,又立下脚跟,还有了如此好的从商机缘,也很舍不得一走了之。
她烦躁地翻了一个身,又想,不过是一个虚名罢了,她何需在意,再者,她和陆远山也勉强算是你情我愿的事情,大不了以后好聚好散,一拍两散!
陆远山甫一进门,就看见岳青宝背朝外,面朝里躺在床上,他伸手翻螃蟹一般把她扳过身来,好笑道:“今天谁惹你了?听说饭都没吃完,就来躺下了。”稀奇得很。
岳青宝一见到陆远山又想起“外室”二字,迅速地又拿背对着他,瓮声瓮气地说:“没人惹我。”
陆远山听她声音不对,问道:“怎么,哭了?”
岳青宝生气道:“哭个屁!”
陆远山手上用力,轻巧地就把她扳过身来,仔细地看她眼睛,见她脸上气呼呼的,却是真没哭,“你一个好好的大家小姐,说话怎么这么粗鲁。”眼睛里却是满含笑意。
岳青宝硬声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
☆、
?陆远山“呵”得一笑,还是问:“说罢,谁惹你了,回头帮你收拾他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