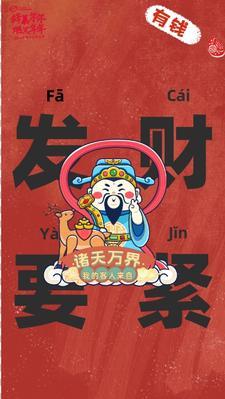UPU小说网>美人瓶叫什么瓶子 > 第15章(第2页)
第15章(第2页)
这时牢头催将起来。三秀便告别了程笑卿,跟着牢头到了外面。
临走,三秀又给了牢头一笔谢钱。牢头接过钱,左右看看无人,方才低声道:“这人,可惜啊。”
三秀隐隐觉得这事不寻常,遂追问了下去。牢头道:“京里的冯府,冯大公子,你可知道?”
“冯大公子告了他?”
“告?哪里能告!三月二十五晚上,冯大公子就死了!这才拿了他。”
三秀大惊。
三秀忘了自己是怎么从监牢回来的。总之等到她一路浑浑噩噩地回来,抬起头,已经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住所。恰是正午时候,天光耀眼。小院还是原来的小院,四望空荡荡的,父亲不在,大师兄也不在,邻人家正在动炊,香味远远飘了来。
无人可商量,三秀也没更衣,便抱膝在槐树下独自思索起这件事。
程笑卿说事关陶小姐。这么看来,他是替陶家人仗义,却又不愿声张,连班主也不肯告诉。他也不肯将这事告诉陶小姐,向她邀取芳心。这确像程大夫的为人。轮他吃几天苦头,他也愿意认了。只是在牢中的他,还不知自己已经扯进了一桩人命官司。
想必是官府查到了那天送别的情形,留心起程笑卿和他之间的争执。那官家也不想想,这程笑卿是个穷酸文人,怎可能对那素昧平生的冯家公子行凶?
“唉,如之奈何,如之奈何!”
她不禁苦恼道。
就在这时,身后的屋门吱嘎一声。
“三秀姐姐,你回来了。”
是瓶娘。这院中剩下的唯一一人正向三秀急急走来。三秀连忙起身。
“瓶娘,有件好事要告诉你,程笑卿他答应——”
三秀想强作出一副笑脸让瓶娘安心,不意却被急走来的瓶娘一把抱住了。
“程大夫给抓走了,”瓶娘低着头,“我都听说了,你是去给他送饭的。”
一炷香工夫前。
瓶娘听见三秀回来,心中百感交集。
她这时候本不该在班里。只是临出门时大师兄说漏了嘴,被她知道了程笑卿给抓走的事,一阵追问,这才知道三秀早早出门是为了探监。遂定下主意,无论如何不肯出门,一定要留下等三秀回来。大师兄无法,只得依她,独自赴会去了。
自己竟是班里最后一个知道此事的人。瓶娘如是想着。自然是三秀怕自己担忧,一直好心相瞒此事。但恰恰因此,此时的瓶娘心中更添了一分沉重——并不是气恼三秀的隐瞒。而到底为什么,她自己也说不清。
直到她听见三秀回来……
她犹豫着。终于丢下手里的针线活计,急急走了出去。
槐树底下,四月风里,三秀安抚着瓶娘的肩头:“傻孩子,别担心,他很好,吃穿都不愁,官差对他也还客气。”
“三秀,”瓶娘终于道,“好姐姐——你待我太好了。为什么要对我那么照顾,让自己那么累?”
三秀的脸微微有些白,她的手也僵了。瓶娘便把她的手握在自己的手心里,望着她的眼睛:
“你为什么不说话了——是不是还有更大的事情瞒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