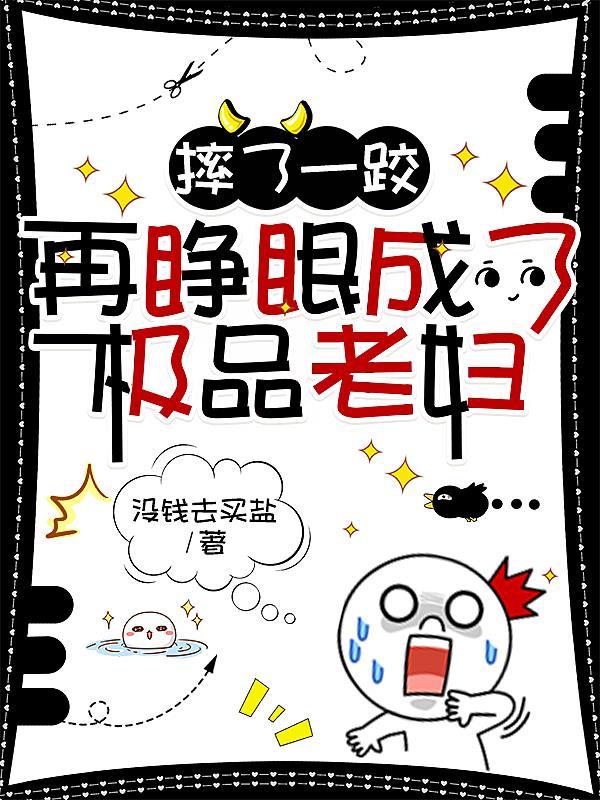UPU小说网>月亮与六便士的象征意义 > 二十(第1页)
二十(第1页)
迪尔柯·斯特罗伊夫应允第二天晚上来找我,领我去那家很可能见到斯特里克兰德的咖啡馆。我得知那家咖啡馆正是上次我来巴黎找斯特里克兰德时同他一起喝苦艾酒的地方,觉得十分有趣。多年以来,他始终在同一个地方消磨晚上的时光,这说明他不会轻易改变习惯,在我看来,这也是他个性的一部分。
“他坐在那儿。”当我们进入这家咖啡馆时,斯特罗伊夫说。
尽管已经十月了,但晚上依旧很暖和,摆在人行道上的桌子几乎满座。我朝人群中扫视了一圈,并没有看见斯特里克兰德的身影。
“瞧,那儿,他坐在角落里,正和人下棋呢。”
我看到一个俯身朝棋盘坐着的人,只露出一顶大毡帽和一把红胡子。我们穿过桌子,来到他面前。
“斯特里克兰德。”
他抬起头。
“你好,胖子,有事吗?”
“我带来一位你的老朋友,他想同你见面。”
“坐下吧,别出声。”他说。
斯特里克兰德瞧了我一眼,显然并没有认出我,把目光又转回棋局上。
他走了一步棋,马上把注意力倾注在棋局上。可怜的斯特罗伊夫惶惶不安地看了我一眼,但我并不觉得尴尬。我点了一些喝的,坐下来安静地等斯特里克兰德把棋下完。我很乐意有这样一个放松打量他的机会。要是我自己来这里,肯定完全认不出他。首先,他的大半张脸都长满了浓密而蓬乱的胡子,头发也很长,不过最令我讶然的是他消瘦了许多,这使他的大鼻子愈发傲慢地凸显出来,颧骨也更加突出,眼睛也比以前更大了。他的太阳穴出现了凹陷,身上瘦骨嶙峋,依然穿着五年前我见过的那身衣服,现在已变得十分破旧,上面污渍斑斑,穿在他身上显得松松垮垮,好像原本是为别人量身定做的一样。我看到他的一双手很脏,指甲很长,手上筋骨毕现,看起来又大又富于力量,但我却想不起他曾有一双轮廓这么完美的手。他专心于棋局,却给我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好像有一种非凡的力量藏在他的身体里。不知为何,他的消瘦更加突出了这一点。
他每走出一步棋,就抬起身子往后一靠,好奇而出神地凝望他的对手。他的对手是一个留着长胡须的法国人,身材肥胖。他看了看自己在棋局中所处的形势,忽然咧嘴边笑边咒骂了几句,恼火地把棋子收拢在一起,扔进棋盒里。他毫不留情地对斯特里克兰德破口大骂,然后唤来侍者,付了他们两人的酒钱,扬长而去。斯特罗伊夫把他的椅子往桌前拉了拉。
“我想现在可以同你说话了。”他说。
斯特里克兰德把目光投向他,其中闪烁着一种带有恶意的嘲讽。我敢肯定他正在搜肠刮肚地找一句戏谑的话,可一时找不出来,便只好紧锁双唇。
“我带来了你的一位老朋友,他想见你。”斯特罗伊夫笑容可掬地把方才的话又说了一遍。
斯特里克兰德看着我陷入沉思,足有一分钟之久。我一直沉默着。
“我从没见过这个人。”他说。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他的眼神告诉我他已经认出我了。但我已经不像几年前那样很容易感到窘迫了。
“我前几天还见过你妻子,”我说,“我想你应该愿意听听她的消息。”
他干笑了一声,眼睛里闪着亮光。
“我们曾一起消磨过一个愉快的晚上,”他说,“那是多久以前的事?”
“五年前。”
他又点了一杯苦艾酒。斯特罗伊夫絮絮叨叨地对他说,我们两个是怎么碰面的,又怎么在无意中发现,我们都认识斯特里克兰德。我不确定斯特里克兰德是否在听,因为他只有一两回好像忆起了什么,抬头望向我,其余时候都陷入沉思。要不是斯特罗伊夫始终滔滔不绝地在讲话,那么这次会面肯定会出现冷场。半个小时之后,荷兰人看了看表,对我们说他得回家去了。他问我是否和他一起走,我想如果我留下来,或许还能从斯特里克兰德那里多打听到一些情况,因此回答说我还想再待一会儿。
等那个胖子离开后,我说道:“迪尔柯·斯特罗伊夫说你是个伟大的画家。”
“他爱怎么说随便他,我才不在乎呢!”
“你能让我看看你的画吗?”
“我为什么要让你看?”
“或许我打算买一两幅呢。”
“或许我不打算卖给你呢。”
“你的日子过得还不赖吧?”我笑着说。
他咯咯地笑了两下。
“我看起来像过得还不赖吗?”
“你看起来像连肚子也填不饱。”
“我就是连肚子也填不饱。”
“那么咱们一起去吃点儿东西好了。”
“你为什么请我吃饭?”
“我并非出于好心,”我冷漠地说,“你能不能填饱肚子与我无关。”
他的眼里又开始闪着亮光。
“那么走吧,”他边说边站起身,“我的确想好好吃上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