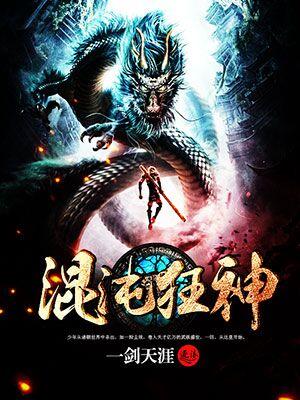UPU小说网>恶毒炮灰的生存准则 > 第35章 裴元清(第2页)
第35章 裴元清(第2页)
难以想象,在这不算长的时间里,他竟然憔悴了这样多,整个人更加的安静,寂寥。
仿佛是,灵魂被抽丝剥茧般一丝丝抽走,渐渐变成一个无知无觉的木偶人。
日复一日,日渐消沉。
直到,再无神采。
见过深秋里的悬铃木吗?那种枯萎的叶子,一片一片掉下来,不过几日间,便光了枝丫。
献祭了深秋。
再无人记得,它盛夏里是何等的绿茵如盖,清爽挺拔。
……
府衙的狱牢并不算大,一路走来,大多是数人挤在狭窄低矮的牢房里,看着都压抑。
裴元清所在的这间还是算宽敞明亮,只有他一个人,墙壁高处,有一扇狭小的窗户。
可以透进来一缕微光。
但不太能清楚的照明,还需要点蜡烛。
犹如一个暗室,有的只有灰暗和湮灭,那点光明,在风中摇曳。
如竹般的君子啊,在这压抑的晦暗里,渐渐消融。
冰雪无法摧毁,却能被夜色暗盖。
朱夫子第一个红了眼,脚步激动的第一个踏进去。
踏进关他学生的牢房。
裴元清还算平静,一撩衣摆,在这还算整洁的地牢跪下,重重向朱夫子磕了一个头。
“起来,你的尊严,老师为你一片片拾起来。”
“绝不会让人平白无故冤了你!”
朱夫子欲将他扶起来,手臂下却是一股拒绝的力量,裴元清摇摇头,不愿起来。
他微低着头,只是沉默着、沉默着。
朱夫子一愣,好似反应不过来,下意识的仍然想拉他起来。
裴元清的膝盖就像是与地面生根了,压根就拽不起来。
朱夫子讶异,低头去看他,眼中似有一片混沌,太多的不敢置信,但更多的是茫然。
霍陵站在一旁,正准备去拉他起来的动作也僵住了。
他们似乎明白了什么,却都是不敢置信。
黎星远远站在门边,面无表情。
一时间,几人皆是沉默。
无边的沉默蔓延开来,在这一片寂静里,却无比扎眼,无比刺心。
朱夫子的手抖了抖,但还是没有放开他。
而是就扶着他双臂的姿势缓缓蹲下,与他平视。
看着他的面孔,他缓缓道:“你七岁的时候,我到你家做客,你父亲当时感叹:“天下何安。”,你说:“治安之本,惟在得人。”
“你父亲又问道:“如何修心人,”你说:“无心者公,无我者明。””
“那时我便明白,你是一个心怀天下,慧心持稳的孩子。”
见他还是沉默不语,朱夫子又道:“你七岁便能做到,明心见性,不滞于物,不困于心,不乱于人,断然不会……”
裴元清打断他,语气平静:“先生也说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如今事临己身,我也无法坦然。”
“明心见性?我做不到,从前做不到是因为不知者无畏,现在明白了,却做不到。”
他只是这样平静的,仿佛是在说他也无法做到是件再自然不过的寻常事。
霍陵听到这儿再也忍不住了,他气急败坏道:“你说得什么胡话,我听不懂!你给我起来!别一副垂头丧气的败家之犬的模样!看着就让人来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