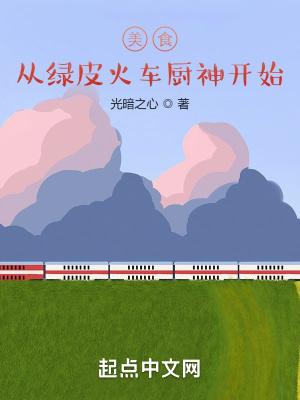UPU小说网>奔月全文免费阅读 > 露曦终身误(第1页)
露曦终身误(第1页)
琬娘每想起那些夜晚,都觉得恍恍惚惚,似幻似真。
她出身本地倡家,家里的姑姑姨姨,都是过来人,除了传授歌舞乐器,也会告诫她:贵人对于投怀送抱者,只要nv孩姿se尚可,气味不恶,来者无拒,可是也不会负责任。一宵欢好后,再见仍是云壤间,陌路人。
琬娘初见荀使君,就有投怀送抱的冲动。边塞军镇,多慷慨英发的武人,可如斯英颀俊雅的文士,却是前所未有。这样年轻,已然大权在握。高高在上,仿佛神仙。
她以为自己是异想天开、花痴疯魔,可是斗胆当着他的面,解下罗裳时,他也便一笑,示意她坐到膝上去。
果如姑姑姨姨所讲。
过程其实并不怎么舒服。他不粗暴,可是也不t贴,一心地攫取她的美好,依然是居高临下,如鹰搏兔。那个时刻,即使她想后悔,恐怕也无法自主了。手腕被箍得紧紧的,身子被钉得牢牢的。那灼烫难耐的痛感,日后忆起,慢慢地会化为甜蜜的渴望。
结束后,他会轻轻拍醒她,“夜深了,我着人送你回家?”
下榻时,腿脚都站不稳。
侍者掌灯,头前引路,含笑提醒:“小娘子小心了,这里是楼梯阶。”
回至家中,阿姨煎了很苦的避孕草药,看着她喝下去,忍不住用指戳她的脑门,“长点儿心吧!”
避孕草药本来没这么苦的,阿姨故意加了h连,意在使她断念。
然而,过了几天再侍宴,又鬼使神差地解了裙带。
此刻,使君微微俯首,沉静地注视着这娇怯的小nv孩,等她开口。
琬娘细声问:“夫人很生气?不会把我们怎么样吧?”
使君的唇角弯了下,“夫人不是老虎,不会吃了你们。好好服侍就是了。”言毕,从容而去。
诸nv伎面面相觑半晌,终于,口直的倩娘说出了大家的心声:“他这样子,就好像不认识我们一样。这叫什么?”
萍娘道:“拔d无情。”
众nv嫌弃脸,“恶,好粗鄙。”
萍娘坚持,“道理是这样。”
琰娘道:“本来就是露水缘,露曦缘尽。”
众nv更不ai听这话,“哎,哎,你这是在说谁的风凉话?”
“我——我自己呀。”琰娘未料到反对意见这么大声,一时语怯,但很快把眉一横,“反正爽也爽过了,又不是一点儿甜头未得。所谓鸟为食亡,nv为情si——”
萍娘注释道:“j情。”
侍者执拂尘出,传召:“小娘子们,使君夫人有请。”
“等着!”琰娘走到窗下文案旁,援笔作书,“待妾给使君夫人补个拜帖。”
拜帖递到戛玉手中,墨迹未g,上书:河yan小红琬、琰、萍、倩等提头践槛,再拜顿颈。
戛玉笑喷酒:“是了,头提在手里呢,只好顿颈。”
乃命入。
荀使君镇河yan五年,使君夫人还是事;以杭州刺史、嗣长安王独山为河yan总管,晋封陇王。
先,独山婚后,请求到外地任州牧,是悫悫妃的主意。
天子很高兴,“你是该出去做些事业了。”先后为他选的湖州和杭州,都是富庶的上州。
此番升迁,依着悫悫的意思,可直接赴河yan任上。独山在曲顺从妻方面,堪称丈夫中的典范。但和明太后思子心切,且yu见一见尚未谋面的孪生nv孙,定要次子夫妇返雒小聚。
悫悫难免生疑,审问丈夫:“是你想回雒邑,才怂恿和明嬢嬢下的这分懿诏吧?”
独山笑着否认,“哪有!”
悫悫哼一声,“也是,你们子母心意相通,何须开口。”
独山帮两nv着上小靴,却坐着不动,直到大nv合合等得不耐烦了,问:“耶耶,不去骑马了么?”
独山笑道:“等等。”
悫悫并不想做一个幽怨之妻,调整心情,也笑道:“快去吧。傍晚还要给牡丹移盆呢,总是你盯着,才好放心。”
独山答应声“好”,这才起身,一手抱一个nv儿,往s圃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