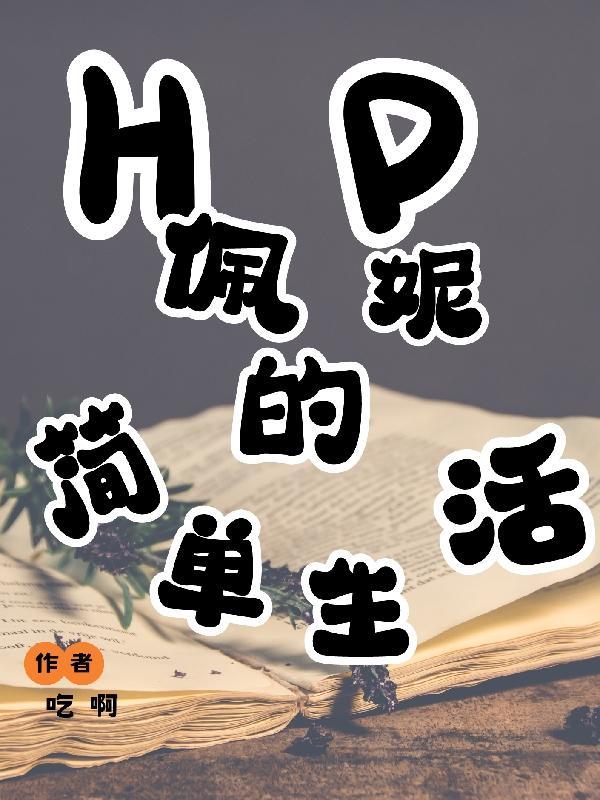UPU小说网>鸡鸣狗吠 > 第二十八章(第1页)
第二十八章(第1页)
华阳公主搞了件大事。
她不知道从哪里,找出来了个韩王遗腹子。
阮青崖推门进了大厅,阮鸾筝已经到了。
听见声响,她微微偏了脸看过来。朝阳从她身后升起,那一点光亮穿过她簪着宝石的冠和晶莹的皮肤,让她在晨间仍略有些昏暗的空间里,泡沫浮梦,海底明珠一般亮——如丝在水,光色灼然。
阮鸾筝问他,“你是来找我兴师问罪的吗?”
阮青崖摇头。
“我就是想告诉你一声,既然话已经说出来给人听见了,那么不管那小子是真是假,我都会杀了他。”
他想了想,补上一句,“就像当初的玉玺一样。”
阮鸾筝嗤笑一声,“你现在都学会拿二哥压我了?”
阮青崖叹了口气,“管用吗?”
阮鸾筝白他一眼,施施然落座。
“先坐下吧。不然一会儿人来了,还又以为我欺负你。”
“什……”阮青崖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说,“没有啊。”
“你闭嘴吧。”阮鸾筝在他面前吨了杯水酒,“有什么话留着呆会儿再说。”
当年阮玄沧奉命带兵入京勤王却临阵倒戈了自己的父亲兄弟,裴齐小皇帝自知回天乏术,不得已奉上了传国玉玺,跪地俯。
传说第一块玉玺是六国一统后所作,此后几个朝代都以得此玉玺为荣,称其为传国玉玺。而每代帝王不但拥有传国玉玺,还会打造自己的玉玺以号令群臣。传国玉玺曾随江山易主,辗转不下十数次,尽尝坎坷流离之痛楚。
所有人都知道,接下来只要皇帝禅位,就能顺顺利利地改朝换代。
但很快内廷里传出消息,说玉玺是假的——真的玉玺已经被人带出宫廷,直到有天号令天下,复国还朝。
……这就很麻烦了。
小皇帝涕泗横流,跪在地上说他没有做假。
可不管他怎么说,似乎都很难保住他这条命了——为了防止裴齐复辟,他的血脉兄弟估计也都活不下来。
禅让的仪式也不得不停止了。
阮鸾筝看着满皇宫将死的人有些于心不忍,“不能找玉匠鉴定看吗?”
阮白野不赞成,“就玉玺的玉料都有不同的传闻说法,玉匠哪里又真的知道传国玉玺是什么样子。除了皇帝,也没人知道面前这块是不是真的玉玺。”
——而皇帝本人,是绝对不会说玉玺是假的。
小皇帝哭得阮绍奇头疼——谋朝篡位的罪名已经够大了,要再加个弑君之罪他怎么着也得掂量掂量。
于是他问他儿子,“你说怎么办好?”
阮玄沧瞥他一眼,把玉玺拿起来端详。
阮绍奇好奇问他,“你能看出来真假?”
阮玄沧看他的眼神像是在看白痴,“不能。”
阮绍奇无奈,刚想说他两句,却见阮玄沧抬手使力,猛地将手中的玉玺砸碎在大殿之中。
那一声巨响,凡是当时在场的人,活到现在都能记得。玉石的碎块噼里啪啦,一时之间滚的到处都是。
小皇帝都震惊的止住了哭声。
阮玄沧拍了下手,语气仄倦,想要把这里的事情赶快处理完。
“玉玺之前已经丢过不只一次了。既然只有小皇帝能给它定真假,那他说这是真的,这便是真的那块,不过碎在战乱里了。外界其他的玉玺,都是西贝货。”
他瞥了一眼旁边记录宫廷事务的史官,像是才想起他来,“你一直在一边记着吗?也是,《左传》有云:‘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而后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世上正是因为有史官这样的人在,世人才可得知分辨真假。”
他说这种话,全场人便或快或慢都看向了史官——好几双形状相近的漂亮眼睛,虽然颜色上有些微差异,但都像肉食动物一样,在宫殿的阴影各处幽幽渗光。
史官站在他们之间,腿肚子转筋,站都站不稳。
阮绍奇笑了,“是啊,所以你我可得谨言慎行,不得造假。”
阮玄沧缓缓地拍了两下在史官的肩膀,看上去慢悠悠的,力道也不大,但要不是他在旁边扶了一把,史官差点没在第二下的时候被拍到地上。
阮玄沧微微一笑,“史官莫怕。想来史家据史直书,纵是被威逼利诱,赔上全家性命,也一字不改。我等诚心敬佩,不敢轻慢侮辱。”
阮绍奇在一边点头,“记得史官上月新得了个小儿子,遇上这样欢喜的事情,我也是不巧事忙,不然该去讨杯水酒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