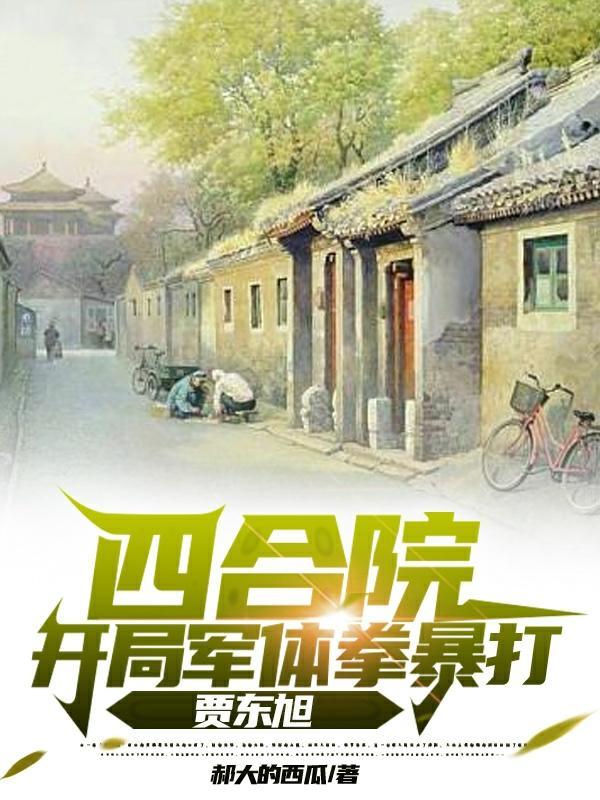UPU小说网>重生凤鸾 > 第76章 父女争辩(第1页)
第76章 父女争辩(第1页)
夜里唐褚过来,与皇后提了一嘴要遣派谢荆去湖广的事情后,便看向唐翘。
“如今朝堂上下提起芝芝便没有不夸赞的,朕甚是欣慰。”虽然这也有他宣扬的功劳在里头,可主要还是他女儿聪慧,他笑眯眯的,不似寻常朝堂上时那样严肃,“芝芝这次立了这样大的功劳,想要什么奖赏啊?”
“真要给奖赏?”她完美承袭了永丰帝和章嫔的优点,不过十三岁,容貌便很是惊人,淡笑时梨窝若隐若现,更添灵动。
永丰帝看着她那一双与自己颇为相似的桃花眼,目光更柔和了不少,“难道父皇还能骗你不成?”
虽只短短几月,他已不自觉喜欢上了这个小丫头。
他很少这样短暂突兀地觉得谁好,哪怕是子女也一样,可唐翘在她这里却有些不同。
永丰帝将这些情绪归结于他对长女多年未尽父亲养育之恩的亏欠。
“父皇如此大方,那女儿可就不客气了。”她双瞳里似有光点微微闪动,嘴角不自觉翘起,跟皇后养的猫儿一样,有一股子不紧不慢的慵懒舒缓。
唐褚看得直心软,“你尽管说来就是。”
她却丢了方才的懒散劲儿,下了软塌来,躬身福礼下去,很郑重:“儿臣斗胆,若最后查明张远所言非虚,父皇可否饶恕与他一同上山为寇的百姓。”
皇后虽然惊讶,却并未阻止女儿。
永丰帝正愕然女儿何以这番举动,闻言若有所思,眸光里映射了灯架上的烛火,眼里意味不明。
“此举虽仁善,可他们一行人触犯大邕律法,更放肆到明知你是皇室公主,却还一意孤行,掳掠于你,将你置于险境。挟持公主以达目的,此已形同谋逆。若轻纵他们,岂非助长匪寇之风,更令皇室颜面扫地。”
后面这句话,他带了怒意。
有对他仁政治理下百姓此极端做法的心寒,更有对女儿遇险的后怕。
“若事情属实,朕会下旨令重治湖州官场,重惩贪官污吏,还湖州一个清明。只是这些人,不可轻放。”
他说的不轻放,重则斩首,往轻了算也是杖责后流放。
后者虽看似有生路,其实却也没有。
她伏身跪下去,“儿臣以为,君子论心不论迹,论迹世上无完人。”
“张远一行人若非信任君心,又怎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远离故土千里迢迢来到京城甘愿落为匪寇,只为见父皇一面,揭露湖广贪污之实。若非被逼走投无路,又怎会兵行险招?儿臣愿意相信,他们是被逼无奈。”
“还请父皇从轻处置。”
永丰帝居高临下望着长女,“皇家威严不可侵犯,他们既做出此等大逆之事,便由不得朕不爱惜他们了。”
语气是不容置疑的,“此事不必再议。你起来吧,另说一个奖赏。”
“只要不出格,朕都答应你。”
永丰帝对子女虽然好说话,却也不会一味纵容,他话说到这份上,已然是极大的宽容了。
唐翘却没起,“儿臣只此一个心愿。”
唐褚霎时眸光凛然,眼里带着怒意,还有一丝连他自己也没有察觉到的期盼,“你为了几个戴罪之身,忤逆君父,这就是你的孝心吗?”
这话就严重了。
皇后连忙拉了拉她,“芝芝,你父皇自然有他自己的考量,你莫要置气了,快起来!”
在皇后担忧和心疼的目光中,她挺直了脊背,“儿臣并非置气,儿臣正因孝心,才有此话。湖广江浙乃财政赋税重地,如今出了差错,不管最后结果如何,经由此次清查,必定人心散乱,父皇小惩大诫以慰民心,此举是为湖广,亦是为大邕江山社稷。”
永丰帝有些恍惚。
多少年了,自他登基至今,已经许多年没有人敢这样与他说话,反驳于他了!
“江山社稷?你一个尚未及笄的丫头知道什么是江山社稷?”他觉得很是可笑,“难道朕这个当了十几年的皇帝,还不如你区区一个入京才三月的孩子不成?”
望着长女倔强的模样,他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朕不过夸你几句,你便这样不知天高地厚,为了一己私欲顶撞于朕。哪里还有什么公主的歉仁模样?”他忍不住怒骂,“你这规矩都学到狗肚……哪里去了!”
多年的涵养叫他死命将险些脱口而出的词语吞了回去,脸色都憋红了。
他努力平复着情绪,告诉自己,这是自己女儿,是长女,是他亲封的长公主。
“朕念你是初来京城,不计较你为罪臣请求之事,此事不许再提!”
他拂袖,终究是不欢而散转身而去,常礼怕他气急栽倒,连忙小碎步跟上去扶着。
皇后顾不上去送他,忙上前去看自家倔牛女儿,“你胆子也太大了,竟这样与你父皇说话,也不怕他真治罪于你。”
话虽这样说,他心里却在骂永丰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