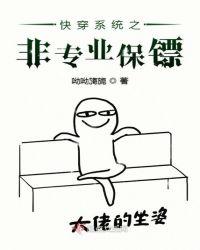UPU小说网>凤皇钗倾颓流年txt > 第57章(第1页)
第57章(第1页)
也许是容絮絮做的吧,也许是别人,宫中的龌龊事太多,不能自保的人,也太多。
但不管是否是她,他愈加相信,这些事的发生,皆因她失职。
作为皇后的本分,她应将后宫整理得井井有条,应震慑众人……总之,她的目光不应该总是在他的身上。
从前的初一和十五,是例行去皇后宫中的日子。
曾是他最烦恼的日子。
因为他已在暗中替她定下失职的罪名,也因为他回应不了她的炽烈。
他的羽翼未丰,朝廷许多事宜,尚且需要倚仗她的母族容家。每每于此,他都为自己羞愧。
他在蛰伏等候一个契机,等彻底可以展翅之时,再不必向她示好。
那一回他问她愿不愿意去北陵行宫避暑。
从那时开始,他就做好了一切的筹谋。布下天罗地网,等待一场丰收。
她那时,不知他的用心,故而很欢喜就答应了。
她不知他要做什么。
对他有威胁的人,太多了,他须将那些觊觎帝位者,一一除去,将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他不可为人傀儡,不可被人操控。
张宋楚三家把控朝政太久,务必斩草除根;梁王扶昀功高震主,绝不可留;他也需要扶植他自己的人,作为最听话的刀,他选择了赵家。
……对于容家,他其实有一点迟疑。
也只是一点,再不能多。有罪当杀,有功当赏,但无论怎样,他们也
不能再掌控权力。
他温柔含笑看着她时,正是在想,或许很快,他也可以更换一位更听话的更合适的皇后。
也许出于那为数不多的夫妻情分,他在北陵行宫,给予她独一无二的宠爱,看似情最浓时,最不可自拔时,如回光返照。
同样是那个时候,他才发觉,她是这样明艳夺目。
在她纵马骑射时,他远在高台上注视她,便在想,世间似赵桃画者众,而无一人能似她。
光彩照人,熠熠如斯,是浓丽绽开的一枝牡丹花,回眸之时,倾国倾城。
倾尽天下文采不足形容。世人谓牡丹之艳俗,但群芳竞绽时,唯有其国色天香,使众芳黯然失色,天地顷失华光。
阖宫上下,看似她对他几乎言听计从,然而只有他自己知道,她和赵桃画她们不同,在潜意识中,他掌控不住她这样的女人,他隐隐觉得,对于他来说,她是和张、宋、楚他们一样脱离掌控的一类人,她不是笼中雀,而是暂困在深宫的鸿鹄。
故而在北陵行宫,他意识到他的一丝心动时,强行遏止了继续的深陷。
这于他而言,太危险,他竟会在意起一个危险的女人,不可掌控的女人。
但世事总非他所能完全掌控,失忆便是一个变数,令他忘乎所以地爱上了这个女人。
他从来不曾想过会和某一个女人白头偕老,或者真心相伴。
但在那个七夕的傍晚,在奉舒镇的小院子里,她牵着他的
手在院落里坐下,替他仔细地梳过长发,一遍一遍,那时他不可自抑地想,他今生,愿意和她过一辈子。
生要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那个时候,他的世界只有她。
美好转瞬即逝,今时今日他复回想,旧日回忆,恍然碎成一瓣瓣锋利的瓷片,每加回想,便割得他鲜血淋漓。
他枯跪半天,雪几乎覆满他的身子,他在崖边,摇摇欲坠,忽然升起极其强烈的念头,他想跳下去——她不会死的,她是那么惜命的女人,她一定不会死,只要,只要他也跳下去,就能找到她!
念头太疯狂了,他眼前只剩下那片单薄的清瘦的白衣影子,他伸手想捉住她——哪怕是一片衣袖也好——他探出身,再往前,再往前一点,就能够到她了。
银甲卫们大惊失色,“陛下!陛下不可——”帝王恍若未闻。
他们只好将摇摇欲坠的帝王强硬拦下,望见这素来以冷漠著称的帝王,此时泪流满面,丝毫未觉。
他哑着嗓子,吩咐:“下山。掘地三尺……生要见人,……”
那个“死”字,如鲠在喉,怎样也说不出来。
他浑身都失去了力气,下山时,颓然将倾,模样被那个奉舒镇的头目瞧见了,头目不知上头发生什么,只管舔着脸问:“陛下英明神武,果然犯人在陛下跟前,绝无遁逃的余地!……”
他好不容易有机会在天子面前露脸,自要大加特加地溜须拍马才
好——殊不知此言刚出,颓状的年轻帝王扫他一眼,复而自嘲地笑,幽幽注视他,嗓音哑得厉害,“她是我的妻子……你知道什么?你知道什么!!”
他毫无征兆地蓦然拔剑砍过去,头目慌忙跪下请罪,四下里雪落纷纷,都慌慌张张地跪了一地。
剑。他怔住,看着剑,这把名剑曾重重伤过她。连剑也突然烫手了,——他慌忙丢开了剑。
痛么,她会痛么!她一定很痛,但她从不喊疼——只会咬着嘴唇,就算疼得死去活来,都不肯低头求饶。
他下了这山。他得清醒点,他要去找她——絮絮,絮絮,你等着我,你要……要等我……他喃喃自念,下到山脚,又摸索着绕去了绝壁的那一面。
崖下正是浩浩荡荡的一条河,横亘在眼前,涛声急切,骇浪拍打在岸边,已是临暮时分,他已痛得忘记了寒冷,忘记了饥饿,忘记身体一切的限制,心中唯一念头,是去找她。
哪怕……哪怕是……他不敢去想那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