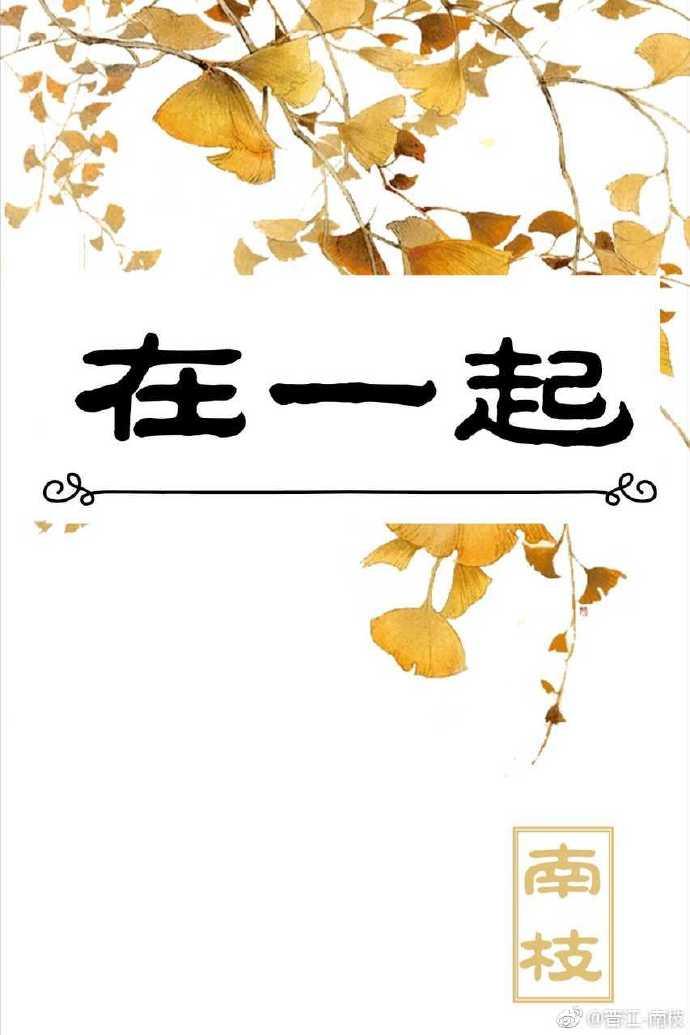UPU小说网>郢州富水txt > 第89章(第1页)
第89章(第1页)
“有客来访,娘子不妨先回去休息,缠头我等待会儿为娘子奉上。”程行礼率先反应过来,对孙云揖礼说道。
孙云本就在看到林怀治一脸要吃人的表情后有些怵,达官显贵、宰相公卿她不是没见过。可这人出现后,席间右相和袁相之子都是噤若寒蝉,脸呈惊悚呆滞,就对此人身份有了大致猜测——皇家。
此时石大娘也快步进来,对孙云招手示意她离开,孙云得意后起身对诸人盈了一礼离开。
站在林怀治身前的郑郁觉得他笼罩在一层阴影下,而林怀治毫不避讳地看着他,脸上那表情就像来抓自己深夜卖春的死鬼郎君一样,恨不得要把人拆皮剥骨。
郑郁想走,可脚下就像生了根一样,被林怀治看得莫名有些心虚。
而诸人看林怀治虽不说话,但周身散发这危险感觉像是要杀人,忙鸟兽散开逃离宴席。刘从祁也扶起有些醉意的袁亭宜,拉着身形摇晃的程行礼赶忙离开。
暮鼓声从门楼处传来,瞬息间人堂内只剩郑郁及林怀治主仆。
郑郁讪笑着说:“殿下安好,时辰不早,臣先告退。”
林怀治瞥他一眼没说话独自往堂外走去,“郑御史,殿下请。”箫宽示意他跟上。
郑郁不解,怎么林怀治来逛这种地方还要我陪着?
“不愿意?”林怀治停步侧过上身问他。
郑郁苦笑着解释不是这个意思,林怀治却道:“不是就跟上。”
说完走出堂内,而箫宽也催他,无奈郑郁只能跟上去。
走出大堂石大娘还在廊下候着,见林怀治出来,便笑盈盈为他引路。这次并未去其他堂内,而是沿着廊下走,偶然路过别堂郑郁还看到了朝廷里几个他熟悉的面孔,内里娇娘笑语,亦有文人墨客正为其赋诗留句。
出得大堂没了暖意,寒意布身,郑郁的酒意也清醒不少。弯弯绕绕走了有片刻,石大娘带他们到一侧门前停下,郑郁听见前方堂内,磬音及歌姬乐声混着男子爽朗叫好声。
“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
“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1]。”歌姬乐声悠悠传出。
石大娘恭敬道:“此处隐蔽,我已让人把守在外,请公子放心。”说完福礼退下。
林怀治留箫宽在外,郑郁见缝插针跟箫宽说,麻烦跑一趟通知齐鸣回府,箫宽看林怀治点头便应声退下。
此刻郑郁不知道林怀治到底要做什么,并不像是来寻娘子谈心的,这大堂是笙箫不绝,歌舞艳艳。他都不知道自己要待多久,不如跟齐鸣说先回去,免得一直在这里等他。
再说在人来人往的红香榭,林怀治就算刚刚想杀人,也不会在这里对他动手动脚,天子居所更不会出现什么刺客。
两人进得屋内,屋内陈设精致原是女子卧房与外面大堂连成一室,只是此刻屋子主人正在大堂奏琴。
林怀治来到一屏风后的榻上坐下,又看了郑郁一眼,郑郁知其意也过去同于榻上坐下。六折裱银高山流水屏风和幔帷前乃是宴饮笙箫之景。
室内光线不明,唯一亮光乃是烛光透过屏风幔帏折映进来,烛光散散。
外头的话声淹没了歌姬的唱句,“林使君押了吴少瑛、宋义、陈月秋入京。人已经在路上了,圣上下旨三司会审,只是过两日就是年关,这事怕是要拖到年后啊!”郑郁看屏风后一中年男子对着主位上语气谦卑。
“唔!我知道。这事出在兖州,林使君是温宗皇帝八子彭王的孙子,雷厉风行这一点上倒是像。”主位上清朗温润的男子应了那中年男子的话,郑郁听那声音颇觉耳熟,细品之后想起一人,平阳世子王台鹤。
继而堂内又人影攒动,一人顿了顿说道:“那陈月秋说这事与宁王有关,不知世子或平阳王能否周旋一二。”
主位上的王台鹤笑了一声,道:“来找我是为了这事?你们也知道京中的事,我父亲哪能插手啊!与其找我不如去找太子,吴少瑛的父亲是可是东宫的官员。”
最初说话那人却道:“世子,太子殿下的性子你也知道,真宋义与吴少瑛勾结上想断冤案,恐怕太子”
“行了,絮絮叨叨的有完没完?这点子事着什么急。”王台鹤不悦地打断了话,说,“不是来请我听曲子的吗?说这些做什么,一口就想吞下整张饼,宁王也太心急了吧?还是诸位觉得张娘子唱的不好?”
堂内官员被这么王台鹤一打断都面上无光,想起今日确实是名义上下帖邀请他来听曲子。说来也怪,平日三请五请都少来的平阳世子,今日竟是如约而至,被他这么一说,诸人皆住口不说这个,继而又开始聊着别的事。
郑郁安静听着,不知过了多久外面传来告辞声,诸人散席。
烛光中林怀治看向他,郑郁察觉目光与他对望,林怀治指了指他手里一直握着的黑布。
这是先前郑郁取下来后,没找到合适机会扔掉,就一直握着,继而林怀治又指了指他的脸。
郑郁懂了,平阳与北阳关系不佳,他在这里王台鹤定心生戒备,随即将黑布蒙在眼上。黑布遮住他的眉眼,只露出他高挺的鼻梁和红润如鲜的嘴唇。
不过片刻就有脚步声向郑郁处踏来,那脚步走至屏风时。郑郁听见衣袍摩挲声,继而是林怀治离榻的声音,随后身上一重。
王台鹤进来时,就见林怀治弯身站着榻前,为一位脸上蒙着黑布的人拢衣服。走进后发现是个男子,看下半脸不免看出是个俊俏人,只可惜是个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