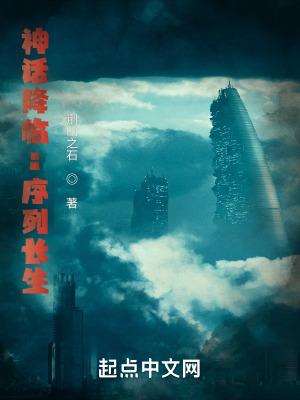UPU小说网>大佬穿进虐文后 七千折戏 > 第二十六章 新岁无眠(第2页)
第二十六章 新岁无眠(第2页)
起码,两人往后还是要合作的,带着怒气步入新年,实在太不吉利了。
这样想着,她开门进殿,动作一气呵成。然而讲和的话未及说,入目便是一副意料之外的人间春色。
——内殿里,羽雁王更衣的动作进行到半,正是个衣衫半褪,赤裸上身的模样。
一时间,两人都愣了。
还是元蔚自己先反应过来。
“你做什么呢你!……还不出去!看什么看!”
他慌乱的扯过衣衫往身上遮,逢上她那副坦荡荡避也不避的眼神,显然都不知该怎么办好了。
裴筠筠被他这一嗓子喊回了神,她挑了挑眉,越看他这样,越是坏心的想要逗弄逗弄。
从从容容的将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圈儿,她啧啧两声,饶有深意的伸出猩红的舌尖,舔了舔嘴唇。
元蔚先是一怔,随即血气上涌,瞬间红了脸。
她强压住笑意,作势要近前,只见他猛地后退一步,竟是拿自己当了恶霸一般。
唉,她叹了口气,想了想,在原地端正站好,中气十足的给他背了遍《登徒子好色赋》。
一篇到头,她还福身一拜,全作致礼。
元蔚都傻了。
打从出娘胎以来,他还从未被人这样调戏
过——或者说,除了面前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死丫头之外,他就压根没被人调戏过。
羽雁王终于还是恼羞成怒了——
“滚滚滚!马上给我滚!别再让我见到你!”
裴筠筠临滚之前,还不住口的嘟囔道:“啧啧啧,又不是黄花大闺女,王孙公子哪个不是被丫头伺候大的,竟还怕人看……”
走出去两步,她忽然回身,朝他做了个嘲笑至极的鬼脸,喊了声:“笑死人啦!”
气得羽雁王一夜无眠。
回到房中,她平静下来,这才将自己心里那点不合时宜的躁动拿出来品味。
羽雁王自幼随父出入军营,十来岁便在军中有威望,年少成名,手里的战功数不胜数——这些话,她耳中听了许多年,可直到刚刚那一眼看去,她才终于有了些真实的体会。
白皙精壮的肌理,本该是养尊处优的清贵,可那一道道纵横无序的刀疤剑痕,却昭示了这样一位天之骄子,为扛起岌岌可危的家门、为担起威震天下的盛名,都经历什么样艰难危险。
那是战场的血雨腥风锤炼出的血性本色,她上一次在人身上见到这等光景,那还是许多年前,自己尚是垂髫幼童之时,在父……
想到这儿,她猛地一睁眼,似乎做了噩梦一般,及时止住了将要四散的思绪。
只是这一夜,她却再难安稳入睡。
过了除夕,没几日便是羽雁双子的生辰。
初五这天,元蔚便将她叫到跟前,同
她道:“明日是我与元隽的生辰,原本我们兄弟也不爱过这日子,今年在孝中,更是不用操办了。”
裴筠筠心道,这还挺省事儿。接着便听他继续道:“明日一早,元隽会启程前往京郊国寺,以先母之名进香祝祷,我要留在府里应对京中人情往来,不便前往,你……”
他顿了顿,两人对视着,裴筠筠听到他犹豫片刻之后,道:“跟他去,替我走一趟,代我进一炷香。”
她当即一愣。
想了想,她直以为自己耳朵出问题了,也说不清心里这会儿是个什么感觉,只试探问道:“殿下,您……没事儿吧?”
元蔚脸色一黑:“我能有什么事儿?支使不动你了?”
“不不不,您可劲儿支使,奴婢哪敢不从!”她先安抚了一句,忖度片刻,心里莫名就觉得不托底:“奴婢就是……就是有些受宠若惊,代替您进香也就罢了,这还是以先王妃之名,奴婢卑鄙如此,只怕是……没这个资格罢?”
元蔚看了她一会儿,一声冷笑就给她噎了回来:“怎么着,这是跟我要名分呢?”
裴筠筠一愣,心中越来越觉得这位殿下有趣。明明是禁不住调戏的人,还偏要上赶子调戏别人,若不是自己大方让着他,还真不知道他敢不敢占着嘴上便宜呢。
“罢了罢了,奴婢可不敢!”她垂眸无奈一笑,领命拜道:“且当之前是奴婢失言,不识抬举罢!主子有命,奴
婢遵命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