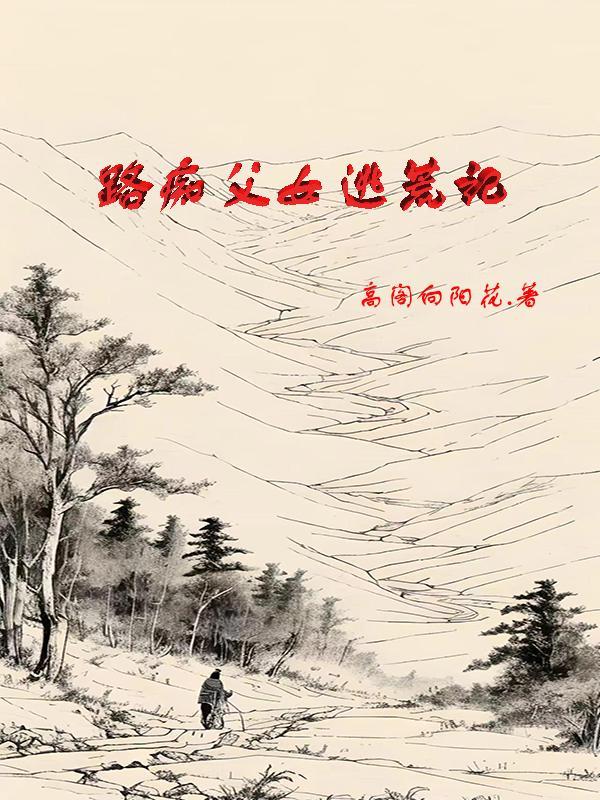UPU小说网>匿名怪咖番外 > 怪咖(第1页)
怪咖(第1页)
连启森开门,连漪跟着进入屋内。
三室一厅的房子,外加一个和厨房相连的小阳台,算不上宽敞,客厅甚至还没有连漪在京市家里的卧室大,十几平米的空间里,墙上挂着前几年从二手市场淘回来的液晶电视,下面是电视柜,墙角落着灰,铺着劣质餐布的餐桌离液晶电视只有几步的距离,短了一截的桌腿被人用几沓书垫着,连漪扫了眼,模糊看见OpenCV什么什么的字眼。
“床单被罩你二婶都给你新换好了,柜子也都给你擦了一遍,有什么不合适的就说,把这儿当成自己家就好。”
稍微大一点的主卧是连启森和谢温在住,另外两个小房间相对着,打开门就能把彼此房间内的装饰一览无余,一左一右紧紧挨着厕所,想不明白房型的设计师是怎么想的。
连漪住的右边房间,她在自己即将要住的房间里转了一圈,然后又一脸嫌弃地走出来。
左边房间门是开着的,连漪往里面扫了眼,极其简单的家具,硬板床,床单铺得皱巴巴的,中间已经被睡掉了色,床边小柜子上搁着烟灰缸,里面堆蓄着许久未曾清理的烟灰,烟头粗鲁倒插在中间,墙边还有个由几支劣质钢管组合搭起来的衣架,上面随意挂着条男人的灰色子弹头内裤,bigsize。
连漪跟被针扎了眼似的嗖一声收回了目光。
没一会儿谢温也回来了,果真和连漪印象中微胖的模样大不相似了,身材单薄,短袖下的手臂瘦骨嶙峋,脸颊微微向内凹陷,背脊也躬了下去,唯一没变的大概也就是柔和朴素的性格。
“是连漪吧,哎哟,可真是好久没见,这么好看了……怎么样,来二婶这里习惯不?不用跟你二叔二婶客气……”
餐桌被象征性地擦了下,连漪来到禾水县的第一顿晚饭就上桌了。
红苕饭,蒜苔炒腊肉,飘着葱花的小白菜豆腐汤,还有谢温买回来的凉拌羊肉。
摆得整整齐齐的凉拌羊肉莫名让连漪想起坐出租车来时路上瞧见的那只死不瞑目的羊,她瞬间没了胃口,草草扒拉几口饭就算了事。
谢温看上去似乎也没怎么动筷子,倒是连启森吃得挺香,还自顾自地倒了半杯自己酿的酒,连漪方才坐在客厅里就观察过那个密封透明的大酒罐,里面泡着枸杞红枣一堆杂七杂八的药物,还有条弯弯曲曲没腿的动物。
三人的晚餐桌上偶尔响起一两句谢温对连漪的关心问候,其它时间只余下连启森稀里哗啦的喝汤声和吧唧嘴的声音,没人提起还应该在场的另一个人。
在连启森喝酒的时候连漪注意到谢温拿筷子的手似乎是抖了抖,只不过她没多大在意,没吃几口就回了卧室。
过了会儿,客厅里响起收拾餐桌的声音,然后开水洗碗,新闻联播又放了会儿,最后卧室门关门的声音响起,是连启森和谢温也回了卧室。
作用不大的空调滋啦啦吹着,下午在超市里喷的那瓶花露水好像也没什么效果,小腿愈发痒着。
床单劣质粗糙,连漪躺得浑身上下都不舒服,被子里满是一股未晒过阳光、潮湿咸闷的味道以及刺鼻的洗衣液香料味,打开手机想找人聊天吐槽,苹果手机信号在小县城里能搜索到的信号少得可怜,好半天才能发出条消息,连漪烦躁地骂了句,把手机用力丢在了一边。
已经来到禾水了,她也就认了,但她干嘛非要和这两位不熟的长辈挤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更别说还有个一天下来连面都还没有见着的异性同辈。
她卡里还有不少钱,干嘛不自己出去租一个又大又宽敞的房子来住?
这小县城虽然破旧落后,但连漪不信找不出一间好房子来,她已经在心底决定好明天就出门自己找房子住去。
这么一想只觉得被子的味道都没有那么刺鼻了,连漪阖上眼,不知道是不是今天经历离奇事情太多的缘故,向来少梦的她竟然隐隐约约做起了梦,梦见多年前夏天,连启森一家人初来到京市她家里的时候——
那时同样是京市最热的时节。
别墅院子里树上蝉鸣聒噪得惊人,听得在客厅里开着空调看电视的她烦躁得很,跳下沙发去杂物室里拿过了打扫卫生阿姨常用的长鸡毛掸子,准备去院子里把树上的蝉全部打下来。
结果一推开门,骤然对上一双冷冰冰的眼睛。
她吓得退了一步,也彻底看清了面前快比自己高半个脑袋的男孩的全貌,皮肤黝黑,头发长长地胡乱耷拉在额前,仔细看里面似乎是还插着草絮毛线之类的脏东西,一双丹凤眼倒是好看,就是眼神又冷又硬和臭石头一样,身上穿着的背心短裤也脏脏烂烂的,下巴处还有结痂的伤疤,和她平日里接触到的家境相仿的小男孩完全不一样,倒像是臭要饭的小叫花子。
再定睛一看,脚边还堆着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这下更是落实了她心中的猜想。
刚好昨天她才看过一则恶魔闯入公主城堡的童话故事,想也没想直接就着手里的长鸡毛掸子向男孩打了过去。
男孩没设防,手臂上顿时被她打出一条长长的红印,本来就没有温度的眼神彻底降到零度以下,抬起头,神情凶恶又可怕,上前来要抢过她手里的鸡毛掸子。
她一边尖叫一边下意识乱打,余光再瞥见脚边的编织袋,用尽全身力气一脚把编织袋踢了出去。
本来拉链就有点损坏的编织袋咕噜噜一路滚到别墅院子中间,终于不堪重负地裂开,其间男孩为数不多的干净的衣服、裤子、袜子、为了来京市专门买的崭新的球鞋……在她慌乱的神色和男孩愤怒拧成一团的眉心中,全部哗啦啦散了一地。
然后她再听到姗姗来迟的母亲祝容的惊呼,以及父亲连启屿严肃责备的声音:“连漪,这是你哥哥!”
这便是她与自己这位远在千公里外的,小破县城里的哥哥的初见了。
后来几十天的暑假时间里,她和这位素不相识的哥哥之间的相处也没有和谐到哪里去。
她活泼大方,他冷若冰霜;她朋友众多,他独来独往;她暗地里嫌弃他、趁大人不在时喊同学来家里玩耍顺带孤立嘲笑他,说他是乡下来抢夺她家财产的小乞丐,他视若无睹踩着他们的欢声笑语从别墅楼梯上去,然后砰一声重重砸上房间门。
-
第二天早上十点,连漪起床的时候家里已经没有人了,连启森应该是又去守着那个没生意的副食超市,谢温估计买菜去了,灶台上的铁锅用锅盖盖着,连漪走过去掀开看了看,一锅给她留的面已经黏成了坨坨。
她嫌弃撇撇嘴,重新将锅盖给盖了回去,打算去阳台的冰箱里找找有没有什么能吃的东西,却没想到在推阳台门的时候指尖忽然传来阵尖锐的痛意。
她嘶了声,发现是自己才做好的半贴美甲勾在了阳台门的铁钉上,甲片一侧已经翘了起来,牵扯着本甲,周围的肉都有些隐隐发白。
连漪心烦气躁,看着自己的指甲,泄愤般踹了一脚阳台门,出门找租房的计划被临时替换成找美甲店。
也不知道这破小县城里有没有美甲店。
最后换好衣服走出卧室的时候,连漪再向左边房间瞥了眼,房间内依旧是空无一人的,昨晚上她也没有听到任何人回来的动静。
她撇撇嘴,不屑收回目光,但又回想起昨晚自己做的梦。
梦境的最后,定格在那年小学暑假比她高出半个脑袋的男孩从她家里离开的场景。
那时她同样趁着没人注意,站在了那个男孩的面前,叉腰恶狠狠道:“小乞丐,以后你不准再来我家。”
“也别想打我家财产半点主意。”
她在说这几句话的时候确实是十分恶毒的,怀揣着十岁孩童不加掩饰的恶意,或许是年纪确实太小了,或许是她真的太害怕了——她知道连启屿和祝容其实一直还想要个儿子,有时祝容甚至会在陪她玩的时候摸着她的脑袋柔声问她想不想要个弟弟。
但两人努力好多年都没有再怀上,她也就慢慢放下心,认为自己仍旧是家里唯一的公主,直到那个暑假这位十八线小县城里的哥哥的到来,又激起了她的恐惧和害怕。
好在男孩也只是待了一个暑假就走了,连启屿和祝容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想要将其留下的想法,可能有,但被男孩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