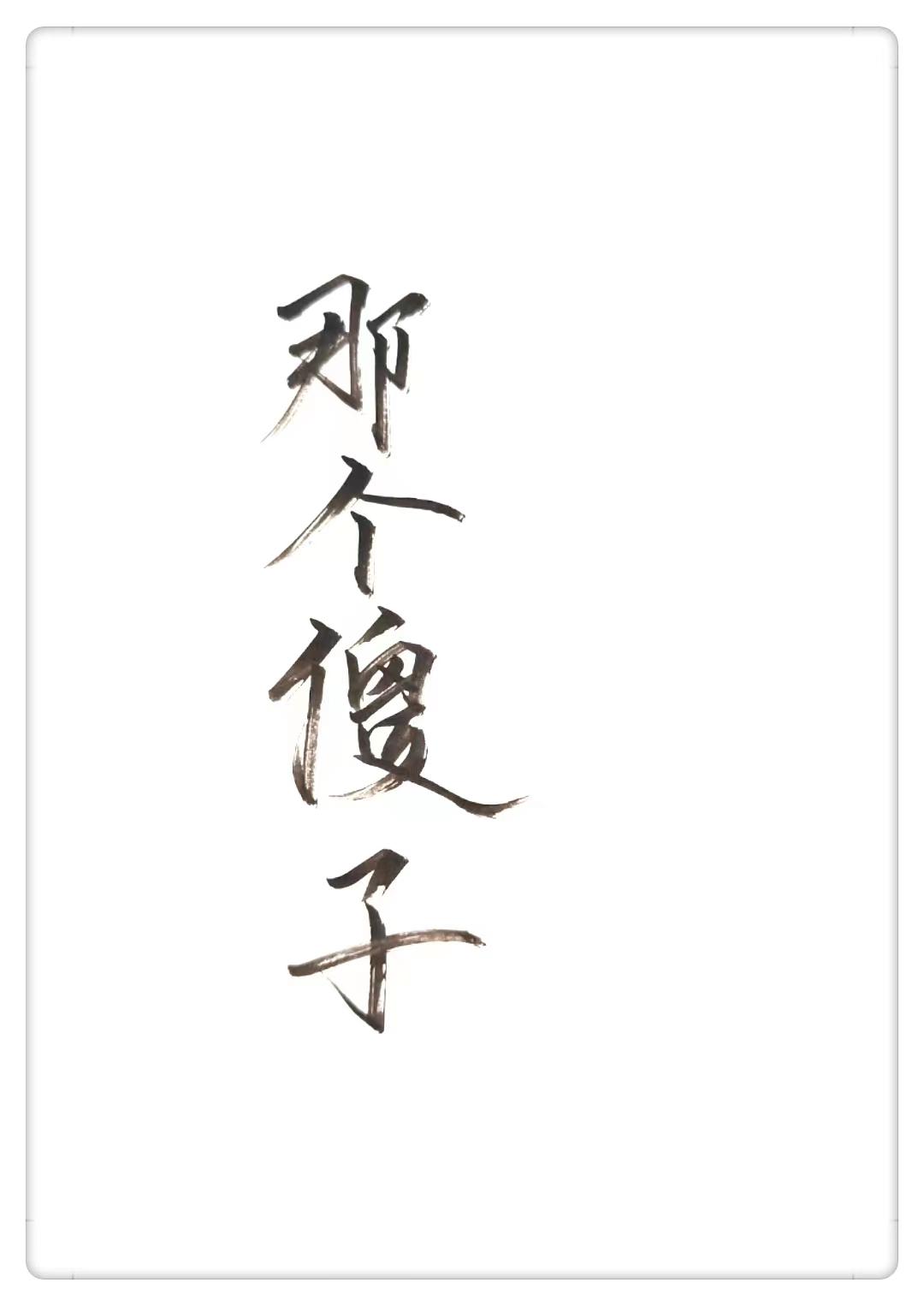UPU小说网>开局拿下钟小艾 一条鱼儿呀 > 第 12 章 扶贫(第1页)
第 12 章 扶贫(第1页)
六点半,天渐渐暗了下去,最后一抹霞光沉到了地平线上,像黑白两界的分界点。
黑暗来了。
祁同伟赞叹这个村子还是和以前那样穷。
没有修的土路高低起伏;大伙还住着以前的土房子;家家户户门口晾晒着鱼干,妇人在院中点着油灯修补渔网,家里男人三五成坐,露着半个褐色身子一边喝酒一边吃着下酒菜。
“你是阿伟吗?”一位老太太在夜里杵着拐杖坐在村口那棵树下,光凭模糊的身影便一眼认出他。
她接受了老阶级末代思想的洗礼,裹着一双小脚,神色淡然,皱纹深陷。
记忆中,她总是这样,每天黄昏时分喜欢一个人独坐在这棵树下。
隔壁村的人都背后说她有病,开拖拉机通过这个村口都会被她吓一跳,像邪祟似的。
本村人都知道,她的丈夫上了战场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她总说会回来的,不论刮风下雨,都在这等着他。
祁同伟这个孩子是她看着长大的,每当吃百家饭到了她家,老太太不在乎媳妇的冷眼,用木梯搭在房梁上,小心翼翼地爬上去用刀切下一块火腿放在祁同伟碗中,用白米饭掩藏。
这个村子没有想象中那样爱慕虚荣,据说很久以前是一个大家族群体迁移,互帮互衬,对他勉强算不错。
祁同伟拎着黑色背包,跪在老人面前和她说了声:“是的,我是阿伟,那个不争气的祁同伟回来了。”
老人笑得十分慈祥,轻轻摸摸他的脑袋说:“好孩子,你已经做的够好了。”
“快些回家,别让爹妈担心。”
“还有,放牛时候千万别再看书了,走路要看路。”
原来,她已经老到记忆出现混乱,记不清祁同伟已经是二十来岁的大学生了。
四年前祁同伟考上大学那时,老太太将政府发放的烈士抚恤金攒了一年,偷偷给了他。
他回到家,家里一切都没变,跟入室打劫后差不多,一片狼藉。
父母看到他的那一刻,误以为是不是太想念孩子都出现了幻觉了,迟疑了数十秒后眼泪再也止不住,真的是他们的孩子。
祁同伟看着这一幕难受,眼前的人陌生又熟悉,父母的两鬓斑白,有了驼背,比以前更脆弱,骨瘦如柴。
两人相互搀扶走到他跟前,母亲哭泣成声,心肉在痛。
“人回来就行,回来就好。”
“孩子,这些年在外头没少吃苦头吧?是爹妈连累你了。”
若不是当年乡上政府工程贪官腐败,偷偷换了劣质建筑材料,去工地干活的祁爸祁妈也不会因为那起事故带走父亲的一条手臂。
祁妈更不会为了寻找父亲,冒着生命危险进去被倒下的房梁压伤腰。
祁同伟年少时多次到政府寻讨说法,结果所有人把这个锅甩的一干二净。
他记住了这些人的嘴脸,尤其是那句话:找开发商去啊,天天像个叫花子一样围在这里算什么?我知道你就是为了钱来的,我们也是受害者!我们找谁说去?
他上哪找开发商去?早他妈卷铺盖跑路了,说不定你们蛇鼠一窝。
后来寻找了许多单位,基本都是互相推脱,再后来他也就认栽了。
从那时起,他就发誓他一定要奋发图强,将来一定要做官!
不谈做什么好官,他没有那么高尚,他只想搞死这群人,还有他深知官是他唯一翻盘的机会,有权自然就有了钱,日子也能跟着好起来。
今后的日子祁同伟这个家的生活水平是一天不如一天。
若不是表弟家雪中送炭,和村民慷慨解囊,他这个家庭或许早就倒下了。
而祁同伟在当时利用业余时间帮助村里人干一些简单的农活作为回报。
村长怜悯他,召集村民开了一个会议,大家一致同意祁同伟吃百家饭,减轻家里负担,再说他在长身体,帮不了一家,帮一个还是做得到的。
他的父母一直靠村民本就不富裕的生活一点点捐助活着。
“爸,你算一下,咋们家这十几年一共欠了多少人情?”
他的父亲在床头柜上放了一本厚厚的笔记本,只要是村里人捐助过的一分一厘他都记在本子上。
今晚,一家三口翻阅本子一笔一笔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