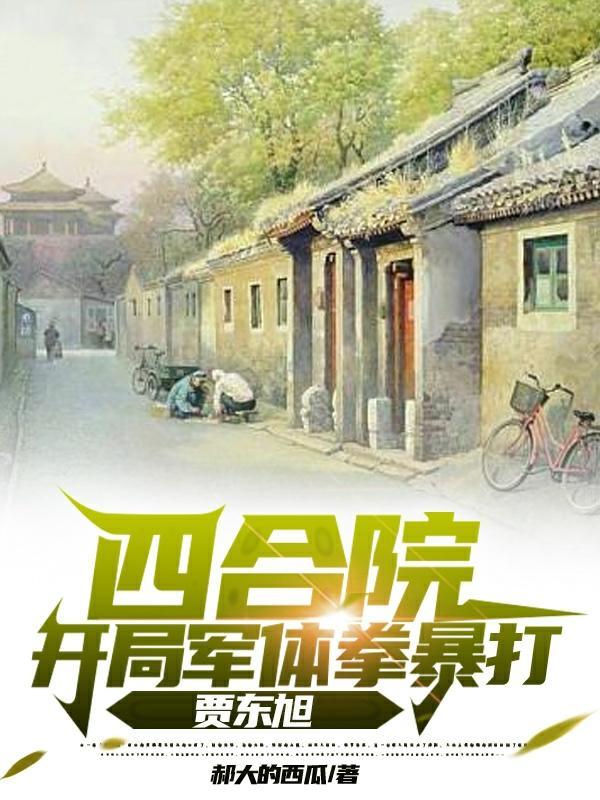UPU小说网>小家小业免费阅读 > 第16章(第1页)
第16章(第1页)
正巧手头没什么事,又见同车都是县城周边几个村的,还有两个熟面孔,于是跟着去了。
那主家的麦地比他屋脚下那片荒野还大。
同去的十个壮年汉子,从鸡叫开始干,管账的就站在地头,看哪个直起腰,马上就说要扣工钱。一天两顿都吃在地里,顿顿杂粮馒头,馒头糙得割喉咙。地头搭了棚子,晚间把麦挑回晒场,还得摸黑回到棚里歇,人还没躺软实,又听鸡叫了。
结结实实干满十天,虽说是结了三百文现钱,可命也去了半条,走回家的劲都没了,只得花十几文搭车回来。
后来他再也没接过这种活。
莫非将麦秆也泡在大缸里,麦秆只需浸泡小半个时辰就好了。
等吃过晚饭用麦秆编些草帽,这个手工简单又不费料,马上天就要热起来了,一文一个应该好卖。
晚上闲着也是闲着。
饭后他先去菜地和屋基地转了转,又将三个草棚清扫整理过,这才点了油灯,将麦秆捞出来,就着被浸泡后的柔软开始编帽辫。
手上重复编着,脑子闲不住,就开始想东想西。
也不知道澄子哥说的小河村人是哪个,他们认不认识那个“冬冬”?那边人少,应该都认识吧
要不要去一趟村长家?就说问玉米种的事,捎带打听一下?唉,打听什么呢
小河村旱了这么久,也在愁水吧?不晓得他家田地怎么样了。
瞧那细胳膊细腿的,若是挑水,可太难为人了,也不知有没有人帮他又关你什么事?
啧,若是兰婶那里真有什么消息,被缠住了怎么办?
还是先躲着?
直说自己还是不想结亲,伤他们的心也就伤了?或是明说,自己打算结契,等几年也不怕?
云山雾里一通乱想,越想越烦,手里的帽辫编得歪歪扭扭,只得起身狠灌了一通水,又在院里跑了几个来回,才能重新静下来继续编。
麦秆用完,莫非看了一下帽辫的长度,大约够缝五个帽子,能卖掉的话,今天饭钱算是挣到了。
帽辫还需用针线缝起来才能变成帽子,这是细活,留到白天抽空再搞吧。
直到莫非再次出发去县城,天都没有下雨。
这几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菜园、挑水和编篮子,田地缺水的隐忧和夜里越来越乱的梦,扰得他每日惶恐不安。
那些不敢深思的隐秘,沉甸甸装在心里。
浅浅几眼,怎么就忘不掉了呢?
可是,这样凄风苦雨的生活,一个人尚且艰难,为何要作茧自缚呢?
园里的番椒苗已经两寸来长,新撒的青菜也冒出了芽头,田里仍是烂泥糊糊的样子。
草帽已经完成,又编了四十几个柳条小篮。
篮子的提手改成了软把的,这样就可以叠放了,再多个也能一次带去县城,这算是莫非总爱胡思乱想的唯一好处吧。
起了个大早,莫非拔了几斤青菜,又将帽子篮子一起叠进大背筐里,盖了草垫,手上也拎了两大串篮子一口气走到县城。
照例先到杏雨饭庄,有什么新鲜东西,他一向先往葛掌柜这里推。
眼见得葛掌柜正跟一个酒贩子在柜上算账,他便先打了招呼,然后立在门外等。
过得片刻,等那贩子满脸堆笑走出门来,莫非才朝葛掌柜说:“葛掌柜,万福!小子又来了,您现在方便不?”
葛掌柜慢条斯理捡好了柜上的东西,慢慢踱了出来才问:“你这带的又是些什么?”
“编了些篮子,看看您这边要不要挑几个。”莫非放下东西,让葛掌柜看个清楚。
篮子新奇小巧,样子也还整齐,是他用了心编的。
“这帽子,手艺不行!啧啧~”葛掌柜先看到了上面的几个帽子。
莫非摸摸头,挺不好意思,“晚上摸黑编的。”
“那你可真是‘瞎编’了。”
“嘿嘿,也是头一回用麦秆,挣几个馒头钱,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闲着就讨个媳妇。”葛掌柜木着脸,居然跟他开了个玩笑。
“这不正攒钱吗?也没有别的本事了。”
葛掌柜把帽子放到旁边,拎起来一个篮子,举在眼前仔细端详,又拉拉把手,好奇问他:“把手为何是软塌下去的?”
寻常的篮子把手是个坚固的圆弧,装在篮子中间部位,方便提握。
而莫非带来的篮子,把手柔韧,与篮身接头处是活动的,用力压下,能凹到篮子底部,拉上来又能立得住。
莫非拿起一个,上拉下压,示范给葛掌柜看,一边细细解释:“我编的时候胡思乱想到的,开始也和以前那样,第二个快编完了,才想到把手硬戳戳太碍事,多几个就不好拿。要是像箩筐挑绳那样是个软的,篮子能叠起来,多少个我都能一把带到县城来,想了好几种法子才改成这样的。这不,今天四十几个全背来了。您别看把手是软的,一样好装东西,拎着也不费事。”
平时他编出两三个,就顺手带来卖了,这次新做的样式其实很简单,挣个稀奇钱,估计很快就有人卖一样的了,所以他后来又去折了许多柳枝,一次编个够,那河岸边的柳树几乎被他薅秃了。
葛掌柜边看边点头:“不错不错。”
他又用力拉了拉把手,看看牢不牢固,“想法不错,你打算一个卖多少?”
莫非听出葛掌柜的意思,慎重地说:“把手再如何也只是个小篮子,何况我手艺就那样,比寻常的多卖一两文,不晓得行不行?掌柜您帮忙参详参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