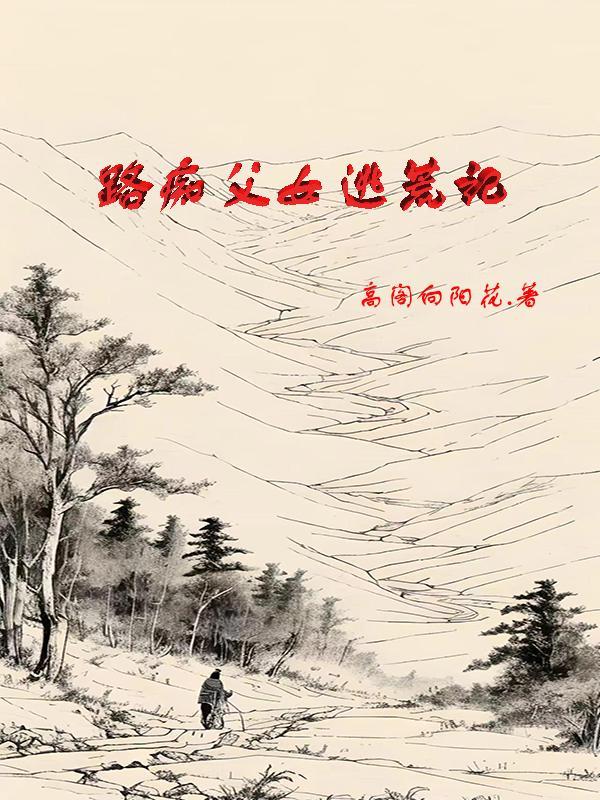UPU小说网>逐明周延嘉明炀 > 分卷阅读161(第1页)
分卷阅读161(第1页)
着了,骂骂咧咧,却没耽误确认这人的模样。
每天走相似的路,见类似的人,说同样的话,日复一日。导游原本以为这钱来得轻松,结果起早贪黑好几天还杳无音信,他现这钱赚得比他带游客累多了。
暮色降临,又一天快结束,他左右权衡,认定这是桩赔本买卖:“张哥,我家里还有事,我要先回去。明天也来不了,你还是找其他人帮忙吧。”
张逐还没明白到底什么意思,对方已经骑着摩托跑得没影了。
他看了一眼挂在天际的夕阳,又看了眼前炊烟袅袅的村落,接着朝下一户走去。
院门打开,里头是个老妇人。按他这几天的经历,这类人最难沟通,还有耳背眼花之类的客观障碍。他简单说明来意,就把照片递过去。
老妇人竟没有直接拒绝,接过去照片,找出自己的老花眼镜仔细看起来。
张逐继续说:“听说你家里住了几个外地人,有没有照片上这人?他是我弟,叫周明赫,他……”
不等他说完,老妇人突然放下照片,情绪异常激动,语极快说着什么,然后抓起他手腕,将他往院子里拉。
这可把张逐吓一跳,他本能地往外挣,问拉他干什么?
老妇人还是一直说,张逐一句也听不懂。突然,老妇翻开自己松紧裤的裤腰,从一卷钞票里数出三张塞给张逐,又使劲把他往里拉。
张逐挣着她鹰爪一样的手,钱掉得到处都是。老妇终于松开他,捡起钱,朝院子喊了两声。
很快,一个扎着小辫的女孩跑出来。老妇和她说了几句,她便用普通话问张逐:“我奶说你在找周明赫?”
“是。你们知道他在哪里?”
女孩接过老妇的钱,再转交给张逐:“我奶说租金不要了,叫你赶紧把他带走。”
四四方方的大院子,一栋三层砖楼朝着南面,楼外贴了瓷砖,四周好些个窗户,看起来有很多房间。
张逐一边往里走,一边听女孩复述她奶奶的话。
说那个周明赫半个月前住进她家,一开始还好好的,见着人有说有笑,每天早出晚归也不知道在干啥。上个星期他就不出房间门了,懒得连饭都不煮。奶奶怕他饿死,就一天给他送两餐便饭。持续了几天,奶奶赶他走,他也不走。没招只好报警,警察过来看他手机身份证都没有,也不知道把他往哪儿送。又说他们收了他租金,至少要让人住满时间。
她奶又着急又后悔,但也不能看人饿死在她屋里。但从昨天开始,给他送饭,他也不吃,天天就那么躺着,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看见有人来找他,简直是看见救星,宁可把收的房租全退,也让张逐赶紧把他给带走。
一楼的单间,房间挺大,却只有四四方方一个小窗,对着后院的柴垛杂物。正中是一张木架床,床尾一个简易桌,旁边是一个老式衣柜,之外再无更多家具。通风不好,站在门口也能闻到一股臭味。
黄昏的光线,穿过遮挡着的小窗投进,把这空旷的房间变得影影绰绰,像是牵连着千丝万缕的细网。而这细网的正中间是躺在床上、背对房门,被子紧紧包裹的周明赫。
他像一个虫茧。
也不知道是停滞太久,蛛网附着到这茧上,还是这些细网,原本就由这虫茧生成。
张逐看着床上那微微的凸起,让他想起羽化失败的蝴蝶,或者这几天他走在乡村小路上时而路过的小小坟包。
他把钱还给女孩:“今天天快黑了,我没法带他走,我们要再住一晚。”
女孩回头和老妇交涉,半晌后告诉他:“可以再住一晚,你必须也在这里,不准你自己走掉。”
祖孙俩拿了钱离开,张逐关上房间门,并从里面栓上锁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