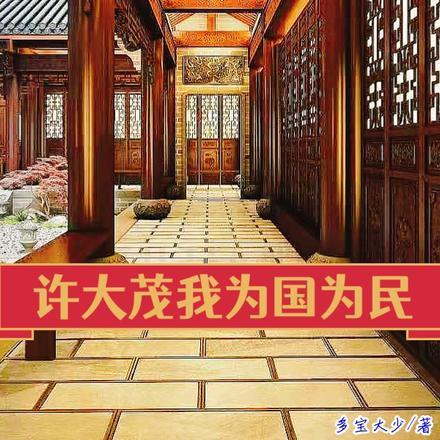UPU小说网>万骨枯其实上一句更经典语录 > 第92頁(第1页)
第92頁(第1页)
周大人問:「殷大安,如今你可知罪?」
他回:「回大人話,草民真心認罪悔過,從此改過自,永不再犯。」
「記錄在案。」
周大人擺手,殷大安起身,走到堂外,跪地,對著百姓又磕一頭,而後老老實實跟著獄卒進獄房,仍舊回後排房幹活去。
看起來無傷無疤,神色平和,下邊的百姓見教化效果如此之明顯,不由得拍手叫好。
張四海悄悄留意堂下圍觀的人,一處處細看,試圖找出一個熟面孔。
周青雲瞧見,再拍驚堂木,指著捧盤,高聲道:「事關重大,殷捕快,時隔四年,未免出差錯,你再上前認認。」
殷若上前,認真看過,舉手道:「大人,我記得清清楚楚:當年麗娘穿的,並不是這一身,她穿的是霜色交領上襦,月白裙子,只有裙邊和右腳鞋底沾到了少許血跡,並不多,不合殺人常理。方才所言之句,若有半句虛的,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雷雨天被劈死的哪哪都有,世人都怕雷公電母,發毒誓通常能取信於人。下邊的人似乎被她說動了,開始低聲議論。堂上之人有意偏袒,並不喝止。
如今孤軍奮戰,只能靠自己,張四海咬緊了牙思量對策,可這會心中又惱又急,堂外嘰嘰喳喳,內外不得寧靜,一時半會,不知該如何是好。
「傳證人胡云娘。」
胡云娘上前辨認過,也篤定地說:「我姐姐要守兩重孝,因手裡銀錢不多,只添了霜色、月白兩匹布,從頭到腳,從冬到夏,都只有這兩色,沒有買過牙色的料子或成衣。這不是她的。」
「記錄在案。傳證人梁四貴!」
梁家管事上前,恭恭敬敬行禮,也上前辨認一番,答道:「那日胡麗娘到訪,想領繡活掙家用,小的不知道她底細,著急打發她走。她捻著袖口讓我看上邊的繡紋,小的因此留意了三分,確實不是這件。」
「記錄在案。」
這個說不是,那個說不是,喊得心更煩。東西確實不是,他們早安排好了一切,胡麗娘瘋瘋癲癲,按說是十分穩妥的。誰能料到這草包閒來無事,竟然把這事翻了出來。
張四海眼看事情要發展到不可收拾,該來的人卻始終沒來,於是指著捧盤,一口咬定:「胡說!我和林捕頭一塊逮到她,她穿的就是這一身。人證物證確鑿,又有她親口供述,這才定的罪。這些人當年都不曾吭聲,如今全冒了出來,必定是受人指使。殷若當年就死纏爛打,非要擾亂公堂,大人怎麼能聽信她一個局外人的說辭,就要……」
「畫押!」
分明是剛才弄出來的血跡,大夥看得清清楚楚。這樣的人,居然管著本地治安好多年。虧他們恭恭敬敬對待,誰知竟是這樣的畜生!
「荒唐!」
「放屁!」
下面的人指著他罵,大老爺氣得發抖,沒有出聲制止。有人忍不住,脫下鞋子朝他砸去。
張四海剛要動彈,高石上前按住。
下邊鬧了一陣,周青雲抬手,站班高喊「肅靜」。
「傳林捕頭。」
林拾一上堂,面無表情拱拱手。
「林捕頭,你來看看,這是否為胡麗娘行兇時所穿?」
林拾一上前看了兩眼,搖頭說:「不是。其時我在外邊巡街,張捕快趕來,說要去抓嫌犯,他說這案子人證物證確鑿,他領先前那位大人的命出來抓人,小的便協同他一塊將胡麗娘帶回縣衙。人證物證全是他搜來的,我也不知為何會變樣。」
張四海氣道:「你……」
林拾一撇頭不看他,張四海怒火滔天,翻身一起,剛要指認他是同夥。林拾一高喝一聲「大人小心」,火敲暈了他。
「張四海狗急跳牆,意圖刺殺問審官,記錄在案,拉他畫押!帶血衣。」
丁三兒抱上來一隻箱子,開箱取出霜色加月白的血衣,拿到外邊亮給大夥看。
「這是當年他們結案用的所謂『證據』。記錄在案。」
底下的人全看了個分明,這樣式、顏色和方才現染的全不同,如果不是心虛,絕不會認錯。由此可見,這真血衣確確實實是假證據。
胡麗娘傷人案事實已然清晰,縣太爺卻沒有喊誣告的人上堂來結案,而是繼續傳證人。
齊忠賢正籌算著上哪弄錢翻修客棧接大生意,在麵攤上又被人叫住。
「齊掌柜,大人說還有些事沒弄清楚,想請你回去交代幾句。」
齊忠賢最會察言觀色,急道:「那契書都簽了,大人不會反悔吧?差爺,你幫著說幾句好話,將來客棧發達了,少不了你的好處。」
「這我就不知道了,您請吧。」
李鐵頭和孔平安領著人從儀門進,這門可不是尋常人能走的,齊忠賢暗自得意——先前那錢沒白送,果然拿銀子敲門,就沒有不開的。
「齊忠賢,當年你說看到了胡麗娘傷你妻室,方才已查明,案子另有隱情。本官再問你一次,你確實是親眼所見?」
當然不是,大人這話明顯在給他暗示。他忙順著這話改口:「回大人話,草民那時太驚慌,並沒有看清,是聽了劉氏哭訴,這才認定。」
「畫押。情有可原,你先下去吧。」
李鐵頭客客氣氣把人請去門房等著,這一幕正好被重帶上堂的甘婆子看清。
小貼士: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或推薦給朋友哦~拜託啦(。&1t;)
&1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