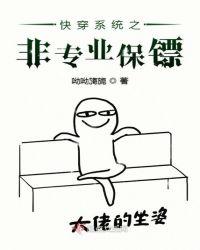UPU小说网>大明女医纪事全文免费阅读 > 第80章(第1页)
第80章(第1页)
“晚辈申时?行,拜见张大人。”
玄衣缊袍的青年郑重朝门房通禀,后者?点头,半晌回来后躬身指引:“请郎君随老奴这边来。”
申时?行撩袍跨入,一路梨花开得好,他却紧盯地面,不敢抬头多视。
“时?行不必多礼。”走至正厅,他才欲曲身行礼,耳畔男子沉稳声音阻道。
又唤了仆从替他将凳子摆好,他推辞数三,终是在仆人的多次相邀下坐了,又赧然地朝上首的男子扯出一个微笑。
“学生携了些许瓜果来与您。”申时?行将手中篮子递给闻声而?来的仆役,“如若座师不嫌,还请收下这份薄礼。”
“学生见师何须携礼?”他听得张居正话中笑意,却是温雅宽和,如沐春风,“但你既然带了来,那我?也却之不恭了,不好辜负了时?行的一片心?意。”
声音如玉石相迸,清朗中含几分沉邃,令他缓缓卸下拘束,微仰起面来视张居正。
甫一眼?,愣怔之色蔓至眉梢。
“时?行?”
张居正见他面有异样,出言提醒。
申时?行回过神,谢罪道:“初识恩师面容,恕学生失态。”
张居正失笑,未接过这话,问以他事:“时?行姓徐,为何又自称为申?这其中可有什么缘故?”
“不瞒恩师,学生乃申氏血裔,祖父过继而?改姓徐,如今学生欲三代归宗,即日便上禀皇帝奏请改姓。”
张居正观其言语谦谨,衣不浮华,早就心?生欣赏:“此乃时?行家事,你自有主张便可,只是改姓事关伦理纲常,你如今夺了天下之魁,一举一动必然牵系四?方百姓目光,多思量此中关节再上疏也不迟。”
“学生也是有此考虑,谢恩师提点。”
“我?也未曾提点甚么,日后走的路皆出于你。但你既为状元,依照惯例当授翰林院修撰之职,你尽心?编史,秉笔直书即可,其余俗事烦忧无需牵挂,适当春秋笔法,亦可见你正直。”
申时?行听张居正话语中肯,忙起身启唇欲答谢,这时?门外走来一年轻女子,双眸往屋里一瞥,展眉笑了声:“贵客来拜访,夫君也不教人坐下,这是甚么待客之礼?”
申时?行善察言观色,闻得这声称呼,立时?弯下腰问候:“学生申时?行,见过师母。”
“原来是状元郎!京城人尽知?郎君蟾宫折桂,恭喜恭喜!”女子挽袖,亲自为其斟了盏茶,暗香随白烟袅袅飘出,笑语道,“今日看了放榜,又思及你与夫君的师生缘分,猜着?你这两日便会来,便特?意从府库中寻出此茶来招待你,申郎君来品品这茶好还是不好?”
申时?行暗思,这娘子应是客套,自己一介商户出身的读书人,如何能让人家夫人这等看重?
他下意识推拒,拗不过她?热情相邀,只得从她?盘中接过一盏,甫入喉,眼?中倏而?放出惊喜神色。
茶叶秀丽带曲,容毫泛白,汤色也清澈透明,尝来鲜爽清香,却是似曾相识。
他抬目讶道:“这……是苏州府特?产的贡山茶?”
顾清稚又替他斟上大半,语调柔和:“看来申郎君还识得故乡的味道。”
申时?行心?中骤然泛起无限思绪,他素来因为家世饱受指摘,自幼所受关爱不多,眼?前这素不相识的女子却能待自己细心?至此。
“谢师母。”那万千感慨流经喉咙化作了简短的三字。
“时?行此次是第一回登门,不妨在我?家用了晚膳再走,我?也是吴人,夫君也爱吃吴地菜,家里的膳食想你应该也能吃得惯。”
申时?行刚欲推辞,仆役又来报:“大人,夫人,有一行登科士子求见。”
顾清稚闻言,含笑视向张居正:“又来了门生拜访你这座师,这回家里可热闹了。”
申时?行忙又起身:“恩师、师母,学生先?告辞,来日定当再行叨扰。”
“哎。”顾清稚眼?神制止他欲离去的脚步,“时?行何必急着?走,提早结识未来共事的同?僚不好么?”
迟疑之间,外客已?至。
“学生拜见老师!”
“问张大人好!”
“师母安!”
数位风采照人的士子共同?踏入,齐齐问礼,望之皆华服翩然,烨然若神人,足见家境之殷实。
张居正一并唤仆役来搬椅子安排坐了,一时?门庭喧闹,谈论之声不绝。
“相公观今日登门的列位进士,可有些感慨?”
“皆为社稷之臣,饱读诗书,精于庶务之学。”
“也是,都是蒙相公评卷拔擢,当然都得往实干之才里挑,只是相公觉得其中哪位最为出众?”
“受七娘赠家乡茶的那位,想你必也是看重他。”
顾清稚抱臂坐于花树之下,看天外阴云忽现,一时?也不急于躲避,气?定神闲道:“我?看他穿着?与另外那几个恍如不是一个时?代,但又耳闻他家境富裕并不缺财,尚能如此俭朴,应该是能脚踏实地做实事的。”
“我?正是如此思虑,当日评卷时?,也是相中其文章切合实际,有利于民生,而?非t?一味讲求文采,但愿其人如其文,合我?期许。”
“公子怎么还在庭前坐着??”乳娘谢氏提着?木桶路过,一见张居正与娘子仍在花荫下对坐闲侃,顿时?老脸泛出急色,“你才伤了风,马上都快落雨了,怎么还不回屋里去?”
“相公伤风了?”顾清稚惊道。
她?趋前去端详,却被张居正起身避开,似乎不愿让她?瞧见:“晨起觉得有些头重,已?是饮了碗汤药驱散寒气?,并无什么大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