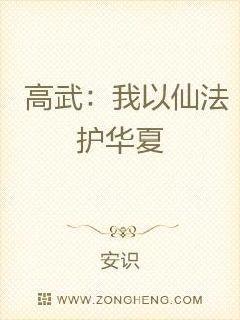UPU小说网>月与河txt > 分卷阅读80(第3页)
分卷阅读80(第3页)
徐姮并没有停下来,走到二楼的她打开了她和徐渚房间里的灯。
眼前是她和徐渚面对面的两张床,中间用一个衣柜隔开,两人的床单都是那种带有牡丹花的老样式,但看得出很干净,甚至她刚刚通了一丝气的鼻子还能闻到一些清新的肥皂味。
虽说是面对面,但只要躺下去,中间的衣柜会挡住对床的所有视线。
徐姮此时回头,现和她只有一步之遥的哥哥用他的黑色短外套兜了很多糖,有徐福记的酥心糖,也有软软的玉米糖,还有一些水果硬糖,一大把。
她的视线从他的糖移到了他的脸。
哥哥那令她熟悉的担忧目光似乎没有从她身上离开过。
他想哄她。
她已经看出来了,甚至这种会被哥哥安慰的预感已经让她的心安静下来了。
徐姮很少会这样感慨,但现在的她就在想:
有哥哥在真好。
徐姮还没说话,徐渚一迎向她的视线就马上解释说:
“……是姥姥让我给你的。”
刚刚姥姥在给客人泡茶端瓜子,的确把他喊过去帮忙了。
徐姮背过身去,指着房间里唯一的一张小桌子,上面有个水果盘,已经被姥姥提前放了一把糖和几个橘子。
至于他外套里的那些,是姥姥给的还是他弄来的,好像没那么重要。
“你放那里呗。”
“我不接,难道你就想一直兜着?”
当徐渚走进房间后,在他身后的徐姮把房门关上了。
两人坐在各自的床边,徐姮从桌上选了一个玉米软糖,撕开放进嘴里就开始嚼。
貌似吃起来比以前甜?
她只是在等哥哥先说话而已。
“没关系的,小月亮。”他说,“下个学期你选理科就是了,妈妈问起来就说是我帮你填的。”
徐姮大概能理解为什么徐渚的安慰总是会让她感到宽心。
因为他很少说虚话,也不试图教道理,他总是会给她一个能解决问题的直接办法,而且理所当然地把所有责任往他自己身上揽。
徐姮有的时候会想,在想如果,就是如果她犯什么事了,徐渚会不会包庇她。
他是哥哥啊,所以会的吧?
当然这只是突奇想,想了还会把自己吓一跳的那种。
嘴里的糖没化完,徐姮又不想在吃了甜的之后又吃带酸味的橘子,她只能沉默地把自己的手指叠在一起,然后又松开,脑袋在瞎想,无所事事。
徐渚从她这里听到道歉很困难,当然想听她的感谢也同样困难。
所以很久之后,徐姮只不在乎地回道:
“没必要。”
她的话听起来可能有点不知好歹,所以停顿了一会儿,徐姮又继续说:
“妈她今晚都这么说了,肯定不会再管了。”
“我今晚……是不是太过了?毕竟是过年。”
她指的是那句口不择言之下说出来的嘲讽朱佩琳的话。
但哥哥也许对她的倔强与带刺早就免疫了,他很笃定地回:
“没有。”
这并不是趋炎附势,也不是在她面前就作出的顺从她的宽慰。
徐渚一向有自己的想法,很早就有了。
“妈妈需要认识到她的经历没有完美到我们会盲目崇拜的地步。”
“她是老师,她已经习惯自己是权威,虽然她肯定做不到否定自己,但她必须认知到逐渐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