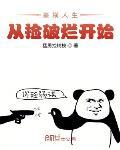UPU小说网>谪宦什么读 > 第83节(第1页)
第83节(第1页)
无论来的人是不是殷无戈,他都必须走一趟。为回岸,为公道。
(本章完)
第86章战未休急之所急。
朔边的战争已经持续了数月,杀场已被清理过,而空气中仍然是弥漫着浓重的血腥气。自朝成立,边军虽说无法杀进寒冷的北境击溃羌族,却也将缘城各方看守得固若金汤。
烽烟台是浓黑色的,此非彼。
“报!司马将军,大军已经集结完毕,是否……”传令兵急急地跑过来。
“且慢,我要再去劝一劝陛下。”司马潜闻言,放下手中的舆图走了出来。
他先是示意传令兵原地等待,而后迈步走向后面的营帐,那是当今朝陛下所休。走在路上,烈日灼不化坚寒,司马潜不由得回想起了三日之前陛下刚刚来到时的场景。
条件恶劣不缺兵卒在路途当中昏厥倒下,而坐在豪华马车上的李延瞻喝着带糖的西域葡萄酿是感觉不出什么不妥的,更何况还带了贵妃前来做伴。
御驾亲征,尤其是来了以稳固著称的朔边北境,说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可偏偏上一代皇上英年早逝,元璟帝急急登位,且不说他对率兵打仗毫无经验,连筹划布局的心思也都还没有应该有的缜密。
跟随来的魏玠倒是老谋深算,可怕就怕在其小聪明都用错了地方,一来到军营,就怂恿陛下把主将司马潜叫来重新布置作战计划,也不知究竟是不是这个理。这里终究是不适合被用来打算盘,也更承受不了满盘皆输的局面。
司马潜不可不斟酌,不可不谨慎。
李延瞻仍是那副慵懒舒坦的模样,随意地挥手令司马潜起身,却也没多看他一眼,而一人躬身站在一旁满脸谄媚,自是魏玠无疑。
这时右边首位的一位身穿甲胄的将士在司马潜的示意之下,上前几步说道:"回禀皇上,属下为司马将军麾下副将任阳,已然奉命打探清楚了,呼延捷所领骑兵四万,步卒八万……”
李延瞻一时面露难色。
李延瞻左右摇摆不定,思索了许久才终于是含含糊糊地道:“所说皆有理,爱将且退,容朕考虑一二。”
表面恭敬却也无可奈何,皇上一来就下了各种各样的备军命令,没任何实际性的作用不说,只要没有坏处也就算得上是大功一件了。可此番断儿戏不得。
帐房内烛光摇曳,司马潜在通报得允后步入内,恭敬对着眼前人,道:“将臣叩见陛下,陛下万岁。”
魏玠也不过是刚刚来到这里,所知甚少,道听途说罢了,且不说消息是否准确,竟还提出让百姓帮守?以为仗着人多就可高枕无忧了不成?何其愚昧。
司马潜眉目骤寒,对于这些身居高堂、不懂得战争残酷之辈,他没有作过多理会,只皱着眉头看了魏玠一眼,便劝诫着皇上道:“臣经三思以为,深入作战一事还需要从长计议。”
听了魏玠的话,李延瞻心感赞同,直了直身子,转脸对司马潜问道:“那就好,准备得应该也差不多可行,如今可探清呼延捷其下兵力如何?”
谁也能听出其中的不悦。
司马潜不能退步,只得尽可能地耐心解释道:“羌戎这么多年来都没能攻入我边,因水网丛林,本就限制了其骑兵的作战效能,加之江河天堑难断。反之,缺少骑兵的我军在北伐时,也同样难以适应,畜运不够而更倚重内河之运,然现下时机实在不适。一来,通坦无遮蔽的平原便于羌戎骑兵驰骋,使我军处于被动,二来河流结冰颇多,航运和作战屏障之能大减,诸多不利。因顾大局,还请陛下收回成命!”
司马潜心下愈寒,沉声道:“战损难填,谁又能确保有失必有得?怕就怕在事倍功半,决策不可不重。”
四周寂静了片刻,李延瞻抬眼瞧他,粗声粗气道:“此话怎讲?”
顾着自己的安危才是头等的大事。
魏玠闻言,在李延瞻身边打了个眼色急急开口道:“陛下,自古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即使损失惨重,如若换得数十年安定,也是物超所值。到时候陛下也必定名流千古!”
“皇上,如今羌族怂弱,我朝大军若是长驱直入,守得安定指日可待呀。何须惧怕这些茹毛饮血之辈!”
“哈哈好!区区数卒罢了,安敢斗胆挑事,朕定要他们有来无回!”人数不及,便判定悬殊,也不知是否片面。李延瞻却洋洋自得,道,“那如今,守城内备情况是否布置完成?”
司马潜欲言却被魏玠抢先打断。只听他胸有成竹一般地说道:“还请陛下放心,水师三万早已经整装待发,破冰渡河也就是一声令下即可的事,居庸城内已经全部戒严,五万守军也已经全部布置完成,如果战事需要,随时可以动员城内百姓上城墙帮守。防线就如同铜墙铁壁一般,倘若南羌的贼人敢来,保管叫他们有来无回!”
这就是在下逐客令了,没让魏玠退,亲疏一看便知。
司马潜只得退下,出帐时和任阳对视一眼,回过身来只见其内影影绰绰如风花雪月,他难掩忧色,心下难定。
烽烟台是焦黑色的,逢人过往时,会被添上一点料子,会是猩红的。····——
街道边的成衣店不见了来往的客人,有的只是借着现成地,换身行头前来办正事的官属役从。
温珧很是拘谨,虽然是被热情招待着的,他还是干巴巴地坐下对着门外守望了大半天,才终于是等到司马厝这个大忙人回来,他猛地站起身来,说:“侯爷,我……”
“听说了。筹出些赈灾银钱不易,卿安费了不少功夫也才逼得朝官不情不愿自掏腰包,难为你一下捐出这么多。”
司马厝先是示意温珧不必紧张,而后随意拉过一张椅子放在身边落座,把腿脚上沾的泥泞擦了擦,抬脸认真地看着他道,道:“都该跟你说声谢。”
“不不不,不是的。云掌印如今下发田作新令,收编遇灾流民入军,侯爷还得忙着亲自督行其令,立信于民。困难不乏,事关重大,我本就理当急之所急,能帮则帮。”温珧低着头,显得很是过意不去,说,“要论起来,我也有责任。州城百姓遭了难,白白挨了这苦头,怎么也挽补不够。”
司马厝深深看了他一眼,未置可否。
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太多了,死再多的百姓,也只是权官眼中的一个数额,不值一提般。同出一门,立场相对,也是少见,温珧和那些人不是一路的。
温珧忐忑地问:“凉州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经这一遭,摊贩摆出来的书卷丹青自是全没了,淹乱中护不住奢侈之物,就算是‘惊天神算,一卦六文’的算店估计也没预料到还能有柳暗花明的时候。天灾总要过去,人祸也能平,那就还会是一日三餐,饭饱衣暖,会好起来的。”司马厝道,“驸马得闲还在练武?”
尽管他只是随口一问,温珧点点头,严肃道:“一直记着侯爷先前说的方法在练的,或许,也该是相较有了长进。让侯爷见笑了。”
司马厝自是没笑。
“可我不知道这样到底算得上是个什么水准,如果上了战场,侯爷估摸着我这能杀死多少个羌贼?”温珧小心翼翼地问。
司马厝沉吟片刻,还是如实告道:“基本功可用于强身健体,过于较真,就会得不偿失了。”
温珧眸光渐暗,难掩失望。
司马厝又安慰说:“征战起将卒纷立,得清平世则生民不复忧。你不用有太大负担。”

![锦鲤穿成年代文女配[快穿]](/img/3907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