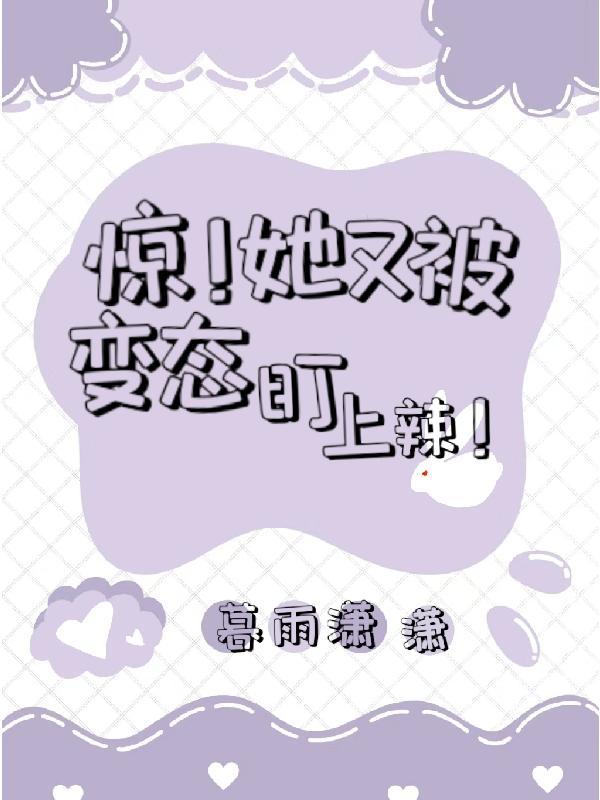UPU小说网>月亮与六便士百度百科 > 八(第2页)
八(第2页)
我一阵迟疑。
“你知道那些人多爱说长论短,”我说,“有人隐晦地告诉我,府上出事了。”
“他跑了,带着一个女人去了巴黎。他把艾米抛弃了,一个便士也没留下。”
“我听了很难过。”我说,不知道接下去该说什么。
上校一口气把威士忌灌进肚里。他大约五十岁,个头很高,身材瘦削,胡子朝下耷拉着,头发花白,有一双淡蓝色的眼睛,嘴唇又薄又平。我印象中上一次同他见面时,就觉得他一副傻相,总喜欢向别人炫耀他在退伍以前每星期要打三次马球,十年间从未间断。
“我认为此刻不宜再打扰斯特里克兰德太太,”我说,“能否请你帮我转告,我十分替她难过?要是她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我很愿意效劳。”
他把我的话晾在一边。
“我不知道她以后该怎么生活,况且还带着两个孩子,难道让他们去喝西北风吗?十七年啊!”
“什么十七年?”
“他们结婚十七年了,”他怒气冲冲地说,“我压根儿就没喜欢过他,当然,他是我的连襟,所以我能忍就忍。但你以为他是绅士吗?她根本就不该同他结婚。”
“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吗?”
“她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跟他离婚。这就是你刚进来时我跟她讲的话。‘把离婚申请书交上去吧,我亲爱的艾米,’我说,‘不管是为你自己,还是为了孩子们,你都应该这么做。’他还是小心为好,日后别叫我遇上,不然我非得把他打个半死。”
我不禁想象,麦克安德鲁上校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因为斯特里克兰德最使我印象深刻的便是他强壮的体格。不过我没有开口说话,毕竟若一个受辱者根本没有能力去惩罚犯罪者,这的确令人痛苦不堪。在我正准备再次提出告辞时,斯特里克兰德太太回来了。她已经擦干了眼泪,往脸上补擦了粉。
“很抱歉,我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她说,“我很高兴你没走。”
她坐下了。我完全不知该说些什么。如果要我谈论与我不相干的事,会让我有点窘。那时的我完全不知道女人有一种永远摆脱不掉的恶习——只要有人愿意做她们的听众,她们就乐于同这个人谈自己的私事。斯特里克兰德太太像是在努力克制自己。
“人们都在议论这事吗?”她问。
我大吃一惊,没想到她竟然认为我一定已听说了她的不幸。
“我刚刚回到伦敦,只碰到了萝丝·沃特福德一个人。”
斯特里克兰德太太双手一拍。
“她是怎么告诉你的,请把她的话一字不漏地重复给我听。”我有些迟疑,她却坚持让我说。“我特别想知道她是怎么议论这事的。”
“你知道人们喜欢捕风捉影。她这个人说的话根本靠不住,不是吗?她说你丈夫抛弃了你。”
“只说了这一句吗?”
我不打算告诉她萝丝·沃特福德在同我分手时,提到的茶品店姑娘辞职的话,于是只好撒了个谎。
“她没有提到他是和谁一起离开的吗?”
“没有。”
“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一点。”
我有些迷惑不解,但是无论如何我现在可以告辞了。我同斯特里克兰德太太握手道别,告诉她如果有任何需要我的地方,我一定为她效劳。她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十分感谢你的好意,我不知道还有谁能帮我些什么。”
我羞于向她表达我的同情,就转身去和上校告别。上校没有跟我握手。
“我也要走了,如果你走维多利亚大街,那么我们同路。”
“好吧,”我说,“走吧。”